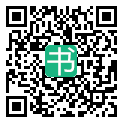第二卷 进士卷
第二章 春江月
那时她哭了很久,却听窗外一缕箫声,是一曲缠绵哀伤的《春江花月夜》,那是温杞的绝技,他用箫声代替自己说不出来的情愫,而她只能用无声的泪水诉说她的柔情。
众人连着那刺客也都傻了眼,都什么时间,你们师生俩个还在玩你问我答?虞璇玑侧头看了那刺客一眼,刺客一凛,这个女子怎么有一双如此明亮的眼睛?虞璇玑问:“老师让学生决定怎么处理他吗?”
那刺客见他长剑在手,心知不妙,只待赶紧将他杀了,又看清虞璇玑不会武功、李千里左臂受伤,知道是个空子,竟是猛下狠招,几次攻向虞璇玑,她只能搂住了李千里闪躲攻击,但是这一带,又使他行动稍显迟缓,虞璇玑一咬牙,趁着一招帘卷长河把刺客架开,她伸手攀住李千里肩头,在他耳边说:“他无心久战,老师只管以攻为守。”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看曲江……记忆里,自己似乎是撒娇一般地说。
李千里点头,她便看着刺客,坚定地说:“壮士快走吧!”
“没错。”这是实情,李千里本来也可以糊弄过去,说根本没这回事不要乱想云云,但是这些日子相处下来,他明白她远比他估计得精明锐利得多,在她已经知道的事上唬她,十分不智。
“知错就好了。”李千里说,伸手摸了摸她的发:“横竖为师皮粗肉厚,死不了,起来吧。”
虞璇玑望着远去的李千里,一片寂静中,水月轻动,大约是有尾鱼游过,划破了水中月影,出现了一条笔直的水线,像是月华往前延伸,蓦地,她想起两句诗来,不禁又羞红了脸。
虞璇玑已经许久没见过这般刀剑相向的场面,真吓出一身冷汗,那道伤口足有七八寸长,半边袖子血淋淋的,她身上也都染了他的血,见他不当回事,情急便说:“谁虑了?自己喝得醉醺醺的,这才着了贼人的道!往后不许喝酒!”
这几日冷得很,冒了风当心着凉……父亲摸着她的头说。
虞璇玑的手僵了僵,什么吻起来没有感觉!呸呸呸!趁座师喝醉酒偷吻他也太纯情了吧?一定是酒喝多了,像李寄兰说的那样‘酒助春情’,还是离他远一点比较安全!
能住回旧家是很好,但是……虽是师徒,毕竟男女有别,住在一起不太好……虞璇玑皱了皱眉,决心推掉:“学生与房东订了契约,需住满一年,老师盛情,学生心领就是。”
虞璇玑惊愕地看着乳母像缝衣服一样在李千里臂上穿针引线,不时看他,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而他苦笑着说:“别担心,不痛。”
“我年纪老迈死不足惜,你却是弑君大罪,你死了,那可怜的小鱼怎么办?好可怜,好不容易找到的靠山竟然垮了,真惨。”
“要不是定陵风水有益子孙,我才不想跟上皇做邻居。”李千里还是死鸭子嘴硬,倒是仔细看了一下地方,有背有扶,对面又看得见陉河,确实是一处好风水。
虞璇玑盯着他,从他脸上看不见一丝心虚或闪躲,看来是真的不知底细了,她叹口气:“这里从前是我家……”
“微臣还是觉得,是上皇想太多了。”
李千里凝视着她坚毅的眼眸,他也无语,在这种时候,说什么想什么似乎都很多余……直到此时,他才察觉她不是他记忆中那个娇柔可人的虞岫嵬、不是一抹柔媚温顺的山雾,直到此时,他才惊觉她的心志刚毅正直如魁斗、情思却缠绵婉转如那一幅绝唱《璇玑图》……他是宦海几度浮沉、刀山火海出来的,而她则是身世飘零久历沧桑,满怀缺憾的他跟带着残缺的她,能不能如他所想,修成正果?
虞璇玑丢了手巾,走出春江亭外,望着亭边曲江池中沦涟的月影,夜风吹散酒意,她按着自己心口,刚刚那一瞬间,望着醉酒的李千里,她想的却是指点她诗文的老师温杞,当年,温杞在京中求官,顺便来拜会父亲试图在西平幕府谋幕职,偶有诗酒唱和,有一次意外地和_图_书见到她的诗,竟特别欣赏她,后来就常来指点她,而后温杞真的去了凤翔,更常来虞家教导她。
虞璇玑伸长手臂接住李千里,设法不让手掌以外的其它身体部位碰到他,但是他实在是太重,只得稍一用力把他往后翻,在头落地之前接住头,然后拉过靠枕来,把他的头放上去。
“如果真有理直气壮的事,你早就跑了,跟到这里才说,表示一定是理由不充分的事。”上皇勾勾手,让后面的内侍倒两杯蜜水来:“说出来我听听,如果勉强还可以接受就放你回去。”
她被休弃的事情传开后,无颜待在西平王宅,恍恍惚惚地乘驴要回南陵,在半路上,一骑从后追来,高喊着她的名字,她回头一看,温杞一声璇玑,双泪落君前。虞家孤微,没有什么显赫亲戚,南陵路远难行,而世上几乎没有弃妇容身之处,她无从选择,只得做了温杞的情人。
“过奖。”李千里剑花一抖,光圆如月:“不趁我适才醉酒无力下手,在我意识稍明后才出手,算得上磊落汉子,为淮西做事,可惜了。”
上皇见他已经开始打量阴宅,便笑着说:“有益子孙是有益,可是你不播种妄想收割不是笑话?”
夜深沉,山亭悄然无声,李千里翻了个身,滚下靠枕,栽到案脚,虞璇玑勉力起身,一步三摇地走到他旁边,重重跪下,把他搬回枕上去,却见案下放着他的长剑,她探身下去案底拿,刚握住那柄乌木为鞘的剑,咦?怎么案下出现了一双脚?李千里明明就在她身后啊?
那头是虞璇玑搬救兵,这头李千里少了顾忌,悠悠闲闲地左挡一剑、右刺一剑:“是哪只鸟派你来的?”
虞璇玑见她那么麻利,便将盘中粗针跟线穿了给她:“要给老师补衣吗?”
“让我猜猜,淮西吴大帅吧?”刺客不语,李千里冷笑一声:“那老屁股就是这样不干不脆的。”
“喂!什么夫人!是女官人!”虞璇玑连忙纠正。
“哼,那几个要不是抱来的,就是晁大帅自己生的!啊我知道了,晁大帅和他夫人是假凤虚凰,他夫人其实是男的,没错!这样就说得通了!”
君臣二人就这样你问我答答了三日,终于上皇在回程走到一半善心大发特许他今日休假可以回去探病,李千里连谢都嫌浪费时间,快马加鞭直奔青龙坊。约莫两个时辰后,终于在山亭下马,就急急往小院赶去。
“喂!都子夜了!还不睡哪!好睡啦!”塞鸿妻的嗓音传来,惊破师生二人的相看无语,塞鸿妻浑然不理丈夫的示意与李千里的怒气,径自扯着他到正堂去更衣:“一身的血,还耍什么帅,伤口好看哪!”
“啧啧,你跟我说话一定要这么下流吗?”
可惜的是,李千里的艳福大概被他造的孽抵光了,就在他隔日入朝视事时,就直接被上皇抓进了祭陵队伍,连跟家人说一声都来不及。于是,在虞璇玑生病的三天中,他被上皇挟持着去了一趟定陵,定陵与西京的距离并不算近,按着大批仪仗队的龟速,朝发夕至已是极限,这几日下雨,驿道难行,甚至几度出现诸官下马推车的窘境,到最后上皇只好自己下车骑马,让后面的军队把车弄出来再说。
醉眼朦胧、泪眼朦胧,她望着远处逐渐变成昏黄的月光在水中晃荡,感觉月光似乎也在腹中摇摇晃晃。这么多年,辗转天下,都是一个人,偶尔学着太白仙人耍帅,自称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可是每回这样都哭得更惨,一个人凄凄凉凉地对月喝酒,越喝越难受。但是酒宴后的寂寞比一个人的孤单更难受,所以她每次都先喝个烂醉,省得去面对人去楼空的凄凉。
李千里意冷心灰绮梦碎,却又不甘心就这么倒下,只得闭上眼睛摇了摇就刻意往虞璇玑处倒,叩地一声额角撞到几案,不管,一定要倒在徒儿身上!李千里忍痛继续装死,果然就在快要撞到地面前,双臂被和图书人架住:“真是!这样很危险哪!”
“好徒儿。”李千里眉尾一动,不敢看她,只怕一分心又闪了神,僵持了一会儿,猛地放开虞璇玑,长身一跃直击门面。
虞璇玑一把扣住李千里下巴,稍一用力掐开他嘴巴,一勺漉酪丢进去,就把整杯的蒲桃酒一起灌进去,然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掐住他鼻子逼他把酒咽下去,这招是她以前请兽医治驴子时学会的:“请老师不要再发酒疯了,喝了这杯就赶快去睡吧!”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春雨连绵硬要出来祭陵,劳军伤财,如果上皇不是陛下之父,微臣必给上皇判个流放岭南。”李千里冷冰冰地看着又凑到自己身边来的上皇。
靠近他,才闻见他身上有种松木的味道,倒不像她那前夫,不爱洗澡总是臭烘烘的,一想起那个混帐王八,李千里根本不算什么恶质臭男人……虞璇玑心气稍平,把他额上网巾拆下来放在旁边,沿着发线擦汗,这才仔仔细细地把这位座师的长相看得清楚。
“老师没打听过这座山亭的主人?”
李千里一个直刺,直击刺客眉心把他迫开,回身就往虞璇玑处跑,右手接过她手中的剑,剑挽平花挡在身前,左臂一长将她圈在怀中,简扼地说:“叫醒家人。”
刺客见他剑势渐厉,剑光如蛟龙回旋上下,衣袂带风,剑之所至,似有寒气划破空气直指心肺,就是惯见生死的刺客也不禁说:“本想你不过一介书生,何须请我出山,眼下看来,你倒是个人物。”
“看曲江。”
“她有名字,请不要随便给她取绰号。”
“在下从没承认雇主何人,官人快杀了我。”刺客倒很镇定,将那长剑往曲江池中一扔,站在庭中。
虞璇玑是士人家庭教出来的超级好孩子……
虞璇玑不敢再看,连忙往回廊跑,几次那刺客就在她身后几步,衣带也险些被扯住,都被李千里阻拦,只得放弃她全力对付李千里,她急急跑到下院去,砰砰砰地敲门叫人。
虞璇玑是士人家庭出身的好孩子……
温杞将她送回南陵,就不告而别,至今,她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如果朝中听不到他的消息,那他大概还在哪处幕府做个小官吧?他今年应该已是五十余岁了,但是,如果他出现在她面前,她还会嫁给他吗?
“呃……”某黑心但是酒量奇差的狗官颤危危地伸出手,指了指虞璇玑又指了指自己。
岫嵬,妳在这里做什么……记忆里,响起父亲带着笑意的嗓音。
温杞貌丑,因此那时年近四十还未能娶妻,听说也曾试探过父亲虞赓的口风,自然被婉言拒绝,而后她成为西平王的六儿媳,温杞没有办法接受她成为少主母的事实,辞官离去。
“再提到海蛎休怪微臣直接送上皇去见太后。”
“真的不痛吗?”虞璇玑问。
虞璇玑起身,正对上他异常温和的眼神,她咬着唇,说不出话……直到此时,她才真正服了他是‘老师’,直到此时,她心中有某一个角落刻上了他的名字,如李寄兰、如李元直、如温杞……只是那个角落到底有多大?她并不知道。
“这么巧?”李千里强忍住笑意,板着脸说:“你我师徒一家,横竖此处为师也只是旬假来住,既是徒儿旧宅,就住进来温书,以备鸿辞科考,为师的若有空来,也可对徒儿讲授一些心得,师徒也好亲近亲近。”
“胡说八道什么!洗一洗伤口好休息了,逞什么狗熊!”塞鸿妻的声音砸破这完美的气氛,李千里忿忿地瞪了乳母一眼,老乳母揪住他领口,直把他往亭子里一扔,后面两个小婢早备好了水、伤药跟用具,刚才虞璇玑去叫人的时候说了他受伤,因此乳母早已备下伤药,果断地撕掉袖子,用清水洗了伤口,又对虞璇玑说:“劳烦小娘子给老妪穿针。”
“你连块田都没有,还播个头?咦?敢情你其实是女人?”
“男人就是这副死德性,酒量这和*图*书么差还不安生。”虞璇玑抱怨着,但是女人总是心软,绝不可能就这样丢着就跑,只得拿过李千里下午时给她搭在肩上的披风过来,帮他盖好,又去拧了手巾来给他擦脸:“要不是因为有师生香火情份,想让老娘伺候你,吃屎吧……”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虞璇玑低低地吟着,在那时,她是真心爱着温杞,是从他那里,她明白原来天下还有人可以那样温柔含蓄地爱着她、欣赏她的才华,不是李元直那样可有可无的引逗,不是前夫的猜疑怨怼与嫉妒:“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上皇嘿嘿一笑,他这几日琢磨下来,大概也猜得出来李千里的心思,只是不说,要看他到底什么时候才忍不住要一诉衷肠。天色渐暗,只见远处几座起伏山峦,已是定陵,上皇便问:“对了,我正想问你,你要跟我葬一起,还是跟宝宝葬?”
“当然不是,棉线丝线会烂,这是桑白皮搓的药线,韧得很,遇血又会融出药汁来,才好得快。”乳母一边缝一边解释,自豪地说:“这可是老妪祖上从太医那里抄出来的秘方,说有个安将军,当年剖腹明志,肠子都流出来了,照样用桑白皮缝回去,活了个长命百岁。”
“二十八。”上皇闷闷地说,忿忿地回头瞪了远处的先帝陵:“可恶,父皇一定知道这件事!一定是他利用晁大帅对他的忠诚,不对!是对他的爱!一定是他逼晁大帅改扮男装的,臭老头!”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剑客本就如此。”刺客苦笑,长剑一振,发出吟吟啸音:“一击不中,无颜再战,官人一剑往我胸口刺吧。”
“看喜欢就买了。”
虞璇玑抱着剑赶出去,抽出剑大喊一声:“老师,在这里。”
“谁担心了?又没人问痛不痛?”虞璇玑脸上一红,转过去,皱着脸看乳母缝伤口:“这是缝衣线吗?”
李千里接过蜜水,一口气喝了半杯,咬咬牙狠心说出来:“璇玑在我家,上皇觉得这个理由充不充分?”
“认识上皇近二十年已经很惨了,怎么可能还愿与上皇地下相伴?”李千里扭头,哼了一声:“可惜陛下竟将定陵让给了上皇,定陵风水比较好。”
李千里盯着他,此人蒙着半脸,目光倒是炯炯有神,不似淮西从前派来的流氓那样猥琐,是个人物,抓他很简单,但是大约也问不出话,杀他也容易,但是毫无用处,该怎么做?身后传来杂沓脚步声,有人奔到他身边,混着酒香的青木香掠过鼻间,他左臂一长,还将那人圈在怀中,分心看了一眼,淡淡地问:“徒儿,为师给妳出个题,这刺客卖了口,抓了问不出话,妳说如何是好?”
“上皇眼睛不好使了吧?没看见微臣的喉结吗?还是等等微臣陪上皇一起去解手,一较长短?”李千里一脸鄙夷地说。
手巾擦过额头,大概是她的四指宽,眉毛生得挺整齐,只是眉心有一些看不太出来的汗毛,有空应该全都刮了才对。单眼皮下长着粗粗短短的睫毛,短睫毛好啊……别像她的长睫毛,总是落到眼睛里。鼻子生得也不错,山根鼻翼都中规中矩,没节没歪,看来应该后势看好,会很有钱。嘴倒是中等大小,上下还算匀称,但是好像太薄了点,吻起来没有感觉……
不……我想试试看蒲桃酒配妳……李千里超级不知羞耻地动着歪脑筋,无奈他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有人杀来绝对可以把他切得碎碎的。他猛地睁大了眼睛,咦?徒儿难道听得懂我的心思?真的要喂我喝酒吗?却见虞璇玑当真走了过来,纤纤素手也伸了过来,李千里心花怒放小鹿乱撞,只觉得她的手指抚着他的下巴,果然喝蒲桃酒是对的,蒲桃酒喝下去口气芬芳啊!
“很痛。”李千里这回倒是老实了。
“谢过老师。”
左臂一刺,却是虞璇玑查看他的m.hetushu.com.com伤口:“好大的口子。”
“旷男的脾气越来越爆了,是不是上回那批海蛎还没消化完哪?”
“横竖是要杀你这狗官!”
“死不了。”
“不充分,没说在你家做什么,继续走。”
“狗官!纳命来!”一声怒吼从头上砸下。
有什么重重的东西落在肩头,虞璇玑仰起头往右后方看,正对上低头看她的李千里:“徒儿,妳在这里做什么?”
虞璇玑默默在心底灌输自己是好孩子,以免自己看到眼前这位用眼神夹她下肚的臭男人时,会抓狂把他爆打一顿。都喝到说不出话动不了只能看她喝的程度,还不闭上眼睛去睡觉,是在这里撑着要干什么?虞璇玑一转腕,镇定地饮下手中镏银杯中的干和蒲桃酒,再舀了匙漉酪和酒吃了。
“不充分,一定是你害她生病了,怎么可以放你回去继续毒害国家幼苗,继续走。”
“没,我向万年县买的。”李千里半真半假地说,这里当然是从万年县手中买下的,但是万年县控有的官人旧宅成千上百,若不是早知是虞氏旧宅,他怎么可能特地买下来?他淡淡地问:“怎么了?”
“进士还没发榜,哪来的女官人?如此狂妄,回头为师就把妳黜落。”李千里的声音无起伏地说,又对那刺客说:“快走。”
李千里无声一笑,薄唇只上扬了一点点,剑转往下,拱手说:“壮士请去。”
虞璇玑一下子忘了男女之防,接过他的手臂,看着那一条蜈蚣似的伤口,伸指轻轻碰触,感觉粗粗的线抵着指腹。乳母见她这样认真地看着伤口,便看李千里,只见他从二十岁起就不大管用的脸部表情,竟然整个松了下来,给虞璇玑一只指头摸一摸,就像猫一样,爽得要打起呼噜来,真是不中用到了极点!乳母正待一巴掌打醒他的春梦,又被塞鸿从旁拉走。
这道伤值回票价!李千里心头雀跃,嘴上还要装潇洒,柔声说:“不喝就是了。”
现在想起来,喝醉后没出什么事还真多亏了她交友谨慎,要不女冠歌妓们在酒席上喝醉被怎么样的事多不胜数,就连李寄兰都曾经差点着了道。
那刺客哈哈大笑,抱拳一揖:“谢过官人!谢过……呃……不是夫人的小娘子。”
“爱徒说了,我岂忍驳她的意?”
虞璇玑是士人家庭严格教导不可以殴打师长的好孩子……
“官人当真放我?”
月光在曲江池边洒下一段短短清辉,虞璇玑叹口气,踱回春江亭去,那位不知道是真醉还是假醉的黑心狗官异常安分地睡着,她盘膝坐在位置上,背靠着扶手,默默地啜着蒲桃酒。烛泪越堆越高,入亭处的几盏烛光早就灭了,她身边的这盏忽明忽暗,只是她也懒得去剪了。
虞璇玑放下他的手,正坐伏拜:“对不起。”
“淮西也买了你的口?”李千里眉头一皱,买口刺客最麻烦,就是活捉了也问不出话。
“想试试看蒲桃酒配漉酪吗?”
“就算晁大帅是女人,他跟上皇也差了快三十岁吧?上皇吞得下去?”
“你会照顾人就跟河朔三镇跪在我面前说‘上皇我错了,请把三镇收回去把我们都流放到岭南去吧’一样不可能,你是想回去做坏事吧?不行。”
“谁说我没播种?”
“谢过官人!谢过夫人!”
君臣二人说到一半,只见一骑追上,是一个军官赶上来:“台主家人送信过来。”
可恶……混帐房东混帐房东!徒儿妳先住进来,为师的帮妳去处理房东,把他丢到黄渠填堤坊好了……李千里心中唠叨,嘴上又不敢坚持,怕虞璇玑识破他饥渴的企图:“可惜了,不过徒儿若偶尔想来住,径自来了就是,为师会吩咐家人安排。”
“晁大帅明明就有好几个儿子……”
“想葬我旁边就老实说,拐弯抹角的,你这别扭鬼。”上皇毫不意外,马鞭一指远处一处小丘:“哪!那块是给你的,不用谢了。”
说着,伤口缝好,用水再擦干净,乳母见虞璇玑好奇,把李千里肿得像猪蹄膀似
www•hetushu•com•com的手臂推过去:“诺!看看老妪的杰作。”锵地一声,虞璇玑只听得金属敲击的声音,很快地,身前身后的两双脚就都离开了她,她被这么一吓,酒醒了大半,连忙抱着剑从案下出来,只见地上血迹点点,兔起鹘落,李千里与那刺客已奔到亭外,只见李千里随手抄了长烛台充作棍棒,拨开刺客的剑,左臂却已是划了长长一道口子。
“璇玑……我貌丑年老,一事无成,妳还年轻不能糟蹋了。”温杞说,痛苦地看着她滚落的泪水,只能呐呐地走开。
说完,便翻墙而出,身手极其矫健,李千里不免赞了一声:“好身手,该请他当护院的。”
“好。”虞璇玑应了一声,瞄见他臂上的伤:“老师的伤……”
但是温杞并没有勇气跨出师生情谊的那一步,即使她抛开了羞怯矜持主动献身,他只惶恐得像个孩子,最后打开了门落慌而逃。等他再回来时,她已穿好了衣衫,向他淡淡一笑:“吓着老师了。”
“伤得不深。”李千里依然面无表情,即使明白这时候应该哼哈哎唷装出一副痛不可当的样子,好吓一吓她,让她给他上药照料,但是若是这样一装,岂不显得是个连点伤都受不住的小孬孬?这样她将来若是考虑嫁他时,不就觉得他不可靠吗?放长线钓这尾大鱼,总得要看远一点才是:“徒儿快去休息,一点小伤,勿虑。”
“老师那时滚下来,其实已经醒了吧?”虞璇玑抿着嘴,稍一冷静把刚才的事情串起来,她就知道自己坏事,当然本可糊弄过去,但是不知为什么,她并不想对他心怀愧疚:“滚下来是想拿长剑,我坏了事,老师才以臂挡剑,没错吧?”
虞璇玑抿嘴无声笑了笑,这么一位肃杀黑心的台主,竟然有个小小的美人尖?不是秃头了吧?她细看了一下,还真的是美人尖,都说美人尖长在男人头上主风流花心,难道座师大人其实红粉知己颇多,无从选择这才不婚?不过也是啦,要不是他在朝中个性这么差,得罪的人又多,一定会是西京士女争相巴结的金龟婿……
“喂!有点礼貌,不过话说回来,是男是女还难说,晁梓隆晁大帅是真男人了吧?可是上回有人提了一大堆证据告诉我晁大帅是女人,我仔细想想,难怪那时候给他裹在战甲里,觉得他胸肌挺有弹性的,又对我这么好,奔蜀的时候几次把我绑在背上,晚上还唱歌给我听,寻常男人哪肯这么做?唉……要早知道他是女人,我当年就该封他个妃召进宫来了。”上皇拍膝拍腿,似乎感叹不已。
“确切来说,是她生了病在我家休养,我要回去照顾她。”
如同所有坊间传奇发展的模式一般,男女主人翁如果在雨中淋个一阵,外带雨中奔跑哭泣等等洒狗血情节后,隔天就是躺在床上愁对一窗凄风惨雨,若是另一个主人翁走进来,躺在床上的那位势必摆出‘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姿态,然后抱在一起大哭特哭接着进入三天三夜行不道德之事的桥段。
李千里拆开信,见是塞鸿妻写的,说知道了他跟上皇去祭陵的事,虞璇玑还在山亭休息,家中安好并无大碍等等。李千里看了信,将信收到怀中,不耐烦地问:“上皇就不能自己去祭陵吗?微臣家中有事哪!”
“微臣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经过小院前面的回廊时,眼角视线瞄到一个身影,又退了回去偷看,只见虞璇玑跪在春江亭的美人靠上面,双肘撑着栏杆、双手托脸往曲江边上看,亭角那块青铜风筝随风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李千里心头一动,十多年前,他也曾看她这样跪在春江亭中……
“补他这块臭皮衣。”乳母说,拈针在烛上烧一烧,掐着李千里的手臂,竟直接在他臂上伤口缝了起来。
“璇玑在我家生病了,充分吧?”
“天凉,别在这里冒风。”粗粗的大手搭在她的额头。
虞璇玑望着李千里,他脸上依然是没有表情的表情:“老师为何买下这座山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