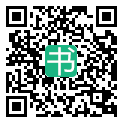第四卷 绿袍卷
第十五章 红颜老
“不是还有我跟姊夫吗?”韦尚书依然口是心非地笑着。
“崔娘……”韦尚书摇了摇头,依然温和地说:“你自小就是这个个性,我也不多说什么,往昔宫人不与外臣通声息,你往东都去,也就是出家人了,还望你来信与我报个平安,让我知道你的状况,若有缓急,也好照应。”
“你担心吗?”韦尚书笑咪|咪地反问。
主父皱了皱眉,崔宫正是他嫡亲表妹,是他引入宫、一路培植起来的,在寂寞寥落的宫城中,是他唯一全心信赖的女人,意志坚强忠心不二,没理由在此时称病不来,他挤出一丝气力:“命她来。”
女皇要说什么,却被萧玉瑶抢先,她颤声说:“老师……你是说,你娶了璇玑姊姊?”
正思量着,却见韦尚书神清气爽地龇着一口白牙走出来,远远就招呼说:“秋霜哪,快来,为师这里有新制揩齿药,快去梳洗梳洗,好入宫了。”
李千里被韦尚书梗得一噎,沉吟片刻才说:“我担心。”
果不其然,内殿里的主父一党把焦点全部放在李千里身上,萧玉瑶的脸瞬间变得煞白,太子首先沉不住气:“李大夫,你不是答应陛下不立正妻吗?什么时候有家内了?”
“韦郎,国老这不是在问李相公吗?你怎么不让人家当事人说话呢?”公主却抿嘴一笑,啼妆上时兴的短眉微拢着,看向李千里:“李相公,虽然已有新夫人,何妨等一阵子后,停妻再娶?再说,若真如你所言,新夫人不受谣言所动,必定是个明理人,她也不会阻拦你更上一层吧?”
“姊姊,我祝你夫妻美满……”那时,她最后这样对韦夫人说:“朕恨他什么,姊姊一定知道,但是,朕无法为难女人……”
“也没说赘婿与正常女夫相同吧?再说,谁说是秋霜嫁给虞璇玑?现在是秋霜嫁给虞里行,律令上没有官人赘婿这个词,所以他是官人|妻。今移天 于虞里行,除了他犯七出,又或者双方协议和离,否则非父母祖父母以外,不能介入婚姻,否则施以杖刑、仍归其夫。很可惜,秋霜与璇玑的父母祖父母都已亡故,所以,这桩婚姻他们两个说了算。”韦尚书有备而来,依然笑嘻嘻地回答,又回头对上皇说:“上皇也见过璇玑吧?是个有担当的好孩子吧?”
李贞一本来不语,此时抬起头来看向妻子想说什么,却被韦夫人一把从后脑打了一掌,又硬把头压下,叱喝道:“浑人!早与你说了陛下是天上紫微星转世,是天仙一般的人物,在陛下跟前需要小心谨慎才是,怎地这般没眼色?作死吗?这才混了个六品侍御史就抖起来了?实实可恨可恼,你没混出个郡夫人与我,死了都不跟你同穴!还不快与陛下主父赔礼!直眉竖眼笔头戳子似的,今夜晚饭不用吃了!本月也无零花钱,勒紧裤带度日吧你!混帐东西!”
“正确来说,是我嫁给她。”李千里心一狠,决定不留任何一点暧昧推托的空间:“虞家仅有二女,需有男子承香火,横竖陇西李氏没有我还有别人,所以我就嫁了。”
“你还颇有自知之明嘛……”韦尚书放下食具,拿出手巾擦擦嘴角,淡淡地说:“不过我既然敢主持你跟璇玑的事,也就不怕你被撵出朝堂。总而言之一句话,御史台主现在还是非你莫属,毕竟一动不如一静,只要你效忠新皇,她也不会非要你做皇夫不可,我们这边,也只有姊夫想成全此事,老流氓是知道你心意的,他不会勉强你。关键是,想抓你到后宫的是褚令渠父子,所以,你只要在他们面前硬顶着抵死不从,也不会怎么样的。”
女皇无语,她知道孙女虽然有些傻气,但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既然萧玉环已经退出,就不可能再遵从她夫妻二人的意思,那时萧玉环逃离东都,就是不愿意奉命嫁给淮西吴元济的儿子,以便朝廷逐步并吞淮西……她回头看向主父,他灰心地转头向内,她心头泛起一阵悲苦,到底是与她结发四十年的男人哪……她一挥袖:“李卿即日起罢中书令,以国老继,李卿与驸马合谋欺瞒于朕,命在家思过,不得出家门半步,以待后诏,退下吧!”
李千里心中一凛,女皇从来没有这样与他说话,但是话中包着话,放在持盈或太子身上都适用,倒是真不好应……他垂下视线,暗自盘算一下,才抬起头,依然是答问礼:“臣自释褐入御史台,至今已逾二十载,御史为人主耳目手足,忠勤王事乃是本分,新君但有差遣,臣并台官自当效命,中书令辅佐君主,亦为分内事,只不知有何事胜于忠君效命?臣愚钝,请陛下示下。”
这是李千里第一次进紫兰殿,他与韦尚书脱了靴子,放在门边,一入正堂,却只见上皇、李贞一、公主与左右仆射、门下侍中等人在一处闲坐,上皇歪在旁边榻上,公主跪在榻上与他捶腿,其余近臣,则坐在榻下,看起来都是神色困顿。公主一抬头,见是韦尚书,眸子一亮,轻声凑到上皇耳边说:“阿翁,驸马来了。”
“骑马不是快些吗?”
外间李千里穿好紫袍,却听韦尚书从帐内出声:“秋霜,我们坐车从玄武门进宫。”
“深呼吸三十次。”
韦尚书闷闷地笑了笑,凉凉地说:“急什么,都走到这里了还没有人来迎……喔,或者说没人来抓,可见主父暂时无事,我们又不是孝子,何需急匆匆地赶去?”
“已在宫中多日。”
上皇哼了一声,摆了摆手算作不计较,李韦师生便与在场众人见礼,公主也下得榻来,难得和颜悦色地对李千里说:“相公拜中书已有数月,未及恭贺,还请见谅。”
那兄弟三人兀自哭哭啼啼拉拉扯扯闹个不休,李千里隐在二门后看,心中却有些担忧。毕竟手足骨肉之情是天性,而今的内侍多是幼年入宫的战俘,与年长宫人内侍结成姐弟母子父子,等到内侍大了之后再与年少宫人或内侍结成兄妹父女父子,内侍间结成父子后便要改从养父姓氏,构成只论姓氏不论出身的血缘关系,宫人葬礼也必须由一名同姓内侍主持,以示有亲人送葬,这都是可理解可包容的人情。
“元辅此行宣抚河北,甚和-图-书是辛劳,驸马协办东都诸事,亦有大功……”女皇照例慰问一番,又问过河北情势后,才命他们坐下,宫人搬来两个坐垫,李韦师生便坐在榻下,其余人便在他们身后身旁坐下,李千里抬头,见主父躺在榻上,一旁坐着女皇,而太子站在主父头侧,女皇又说:“朕有一事欲嘱托元辅,不知元辅能受否?”
李千里脑中灵光一闪,稍定了定心,便平手在胸:“禀上皇,此事微臣虽有寸功,却远不及家内于魏镇调停斡旋之功,她击退淮西说客、又哄得……”
“能被我捉弄后还好整以暇说‘那是要下官摆酒恭喜二位吗’,这孩子是颇有胆识不错啊……”上皇拈着胡须,笑眯了眼。
“老师难道不担心我真的被撵出朝廷吗?”李千里皱着眉问。
“我没说她是。”
凝碧池是东都宫中的大池,前几代先帝往东都时,常于池畔泛舟游玩,而上阳宫则是东都城南的一处离宫,明皇帝时的杨妃不愿旁人分宠,便将许多貌美宫女赶到上阳宫中。只是不管凝碧池或上阳宫,都是皇帝不会再去的地方,没有出路没有未来,红颜白发,也没有差别了。
“没有。”李千里僵硬地说。
崔宫正闭了闭眼,微一躬身便离去,韦尚书目送着她离去,一叹对李千里说:“凝碧池畔红颜老,上阳宫中白发新,大约也就是如此了。”
韦尚书、上皇与太子、太师等人在旁边看得下巴都快掉下来,李千里不是没被女皇当面指出错误跟疑似有罪的地方过,但是他总是死鸭子嘴硬,千方百计最后就是不认罪,此时这般干脆,实在是太不像他了。
李千里首先回过神来,此时已过午时,迟迟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李千里拱着手,那环紫玉映着午后的阳光,边缘的一线光芒,像在提醒着什么。李千里吸了口气,决定快刀斩乱麻,强挤出一丝微笑:“郡主有心为国效力,甚是难得,家内若是得知郡主便是玉环,也必定欢喜。”
宰相虽然不至于天天见到女皇,但是谁也不想因为体臭口臭被女皇讨厌,所以相臣人人都勤于梳洗,李千里自然也不例外,而他的座师大人更是热衷此道,韦尚书是天生鼻子灵敏,据说连藏在衣箱底的死老鼠都闻得出来。李千里依言入内,韦尚书一脸好事相报的表情,把自己做的揩齿药打开,李千里只得谢了,抽过一根削过皮、泡着温水的柳枝,把枝头咬软、咬出纤维来,用银匙舀一勺揩齿药放在手心,沾水沾药擦牙,如此再三,最后再用水漱口。
梁国宫廷除内侍外,良人出身的宫官、宫女与贱民官奴出身的宫婢,分属六尚局与宫正管束,六尚仿外廷六部而设,为尚宫、尚寝、尚食、尚仪、尚服、尚功六局,各有职司,而各处宫殿的宫女虽由妃子使唤,但是惩戒、纠举之权仍属宫正,可说宫正便是内廷的御史台与刑部。而六尚主官与宫正虽品阶都是正五品,但是宫正因为职掌宫规,地位自然较六尚为高,宫中一向有惯例,颁赐年资较长、素行正直的宫人‘女尚书’之号,因此一般也多称宫正为尚书。
女皇从未遇过这般唠叨妇人,也不知怎地,听她插科打诨啰哩叭嗦,竟然气平了,然后也不知为何,就喊了她一声‘韦姊姊’。这么多年,她想李贞一、恨李贞一,却怎样都无法恨韦夫人……
“新皇上任,谁也不知会不会清算吧?”
“学生只知道赞皇公与陛下过去有情,却不知主父与赵郡夫人也相识?”
这几人中年纪最长、身着绿袍的内侍直起身,果断地说:“儿等幼时自岭南入京,举目无亲,唯有阿母于掖庭中提携褓抱视如亲生,虽无生恩却有育德,纵有亲母,有怎及得阿母一分?阿母且行,儿等随后便请调东都,好侍奉阿母。”
“但愿如此啊……”
“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人主大怒必是臣下有失,夫君有过则是妻未尽劝勉之责,只不知陛下因何事龙颜大怒?”韦夫人冷静地问。
“三姊从前说‘贞一如修竹在柳林’,看起来颜色一样,风姿却大不相同,我自幼便认识他,但是到现在,还是不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人。”韦尚书抚着胡须,紫兰殿已然在望:“对三姊好得不能再好,但是饮酒狎妓也没拒绝过,抚养一大家侄儿外甥,但是来投靠的亲戚却不太理睬。我那外甥,小的时候提携褓抱,结果现在人丢到忠州去,也就不闻不问了,奇怪了,阿宪又有哪处不如人了?还不准我调他回朝,真不知他心里头想什么,大概是老糊涂了……”
“他欺负我三姊算过节吗?害我三姊被姊夫误会,险些孤老一生算过节吗?如果这算过节,我想我一直想把他赶出朝廷应该不为过吧?”韦尚书走出帐外,已是一身鲜亮,笑嘻嘻地说。
“秋霜与陛下早有约在先,就是娶了虞璇玑,也只是妾不是妻。”李贞一完全无意纠正上皇低落的文学水准,淡淡地说:“持盈郡主还是得娶。”
那宫人迟疑地应了一声便离去,主父合上眼睛,歪过头睡去……
女皇那时看着李贞一竟然娶了个万事不如自己、又穷凶恶极的泼妇,只觉得又悲哀又伤感,却听韦夫人连连叩拜:“拙夫是只骡子,看来像马其实是驴,只外表好看,回家后又埋汰又脏污,饮酒狎妓样样来不说,还偷藏私房钱不让贱妾知道。说起来也是贱妾眼拙,毕竟是个再嫁之身,又不貌美也不年轻,还有个成年的女儿,实在是无人可挑了,那日他饮醉了,贱妾便……唉……总之,虽是贱妾押着他成婚的,但是完全不是什么心心相印,不过他背运些又不甚挑剔,横竖是个老旷男,也就凑和着……贱妾知道陛下为人妇、为人母还得照料天下,实在是古往今来第一辛劳的女子,但我大梁能有陛下,真不知与我等妇人出了多少恶气,否则这些埋汰臭汉都将女人看扁了,贱妾日日烧香祈求上苍保佑陛下千秋万代,最好往后世世代代都是女人当家才好……啊,话又说回来,贱妾此来,是求陛下赏个旨意,不许他出去外头饮酒作乐,若出去被妾逮到,贱妾便可管教,所谓‘奉旨教化’也,求陛下降旨……和图书”
此语一出,李韦师生便确定公主与李贞一是一路的,李千里倒也早有心思,一咬牙,脸上微微一动:“臣为性命之故,不敢停妻另娶。”
“禀上皇,臣与恩师得命后,日夜兼程,不敢担延。”
“二相因何不走端门?请出鱼符勘合身份!”
李贞一只稍稍一楞,犀利的目光盯着韦尚书,毫无商量地说:“就算是秋霜嫁给虞璇玑,男女依然有别,他不是虞氏妇是虞氏赘婿,赘婿在律令上,只是继承的最末位罢了,其余并无规定与正常女夫不同。”
“我已经呼吸到第二十七次了。”……
“痴儿、痴儿,你已寻得亲母,往后要好生奉养,我不过是当年稍待你好些罢了,莫要挂记,且去奉养亲母为好……”老妇婉言相劝。
韦尚书与公主一问一答,把目前状况问个明白后,李贞一从旁插过话来:“秋霜,你们在关东河北的事怎么样了?”
等到李韦师生二人翩翩然、施施然出现在玄武门外时,玄武门外正在操练的神策军与左右羽林军中,窜出数骑直赶过来,高声喝问:“何人擅闯禁苑!”
女皇、李贞一与主父却面色古怪,李贞一冷着脸,目光朝下,女皇白着脸,直盯着李千里,而主父容色惨淡,悲伤地望着头上梁柱。当年女皇听说李贞一娶了韦氏时,嫉妒欲狂,威胁于他,而主父躲在殿后听到他们的对话。当时,李贞一说的话,与李千里如出一辙,是那番话,让女皇伤透了心,恨得拿剑要杀死他,而主父赶出来,夺下她手上的剑……
在那场拉拉扯扯的混乱中,李贞一如今日李千里一样,伏拜在地,不发一语,但是那直挺挺跪在地上的背,对这一生全被宰臣父叔等男人控制的女皇来说,有如无声的抗议与嘲笑,笑她不明白人间疾苦、不明白男人的苦衷、不明白这世界本来就不是女人该来作主!
李千里默默不语,他知道当座师大人自吹自擂自家的揩齿药、澡豆、香丸、面药、口脂……等清洁芳香用品时,最好就是闭嘴让他讲,讲完了就好了。所以他耐心等到韦尚书讲完,才把刚才所见所闻说来,韦尚书目光一闪:“哦?窦中尉的干亲家,那一定是崔宫正无疑,崔宫正掌内廷戒命刑律近三十年,倒是一直对陛下忠心不二,她被赶到东都,我却不曾想到……”
崔宫正见韦尚书,一时间竟恍惚了一下,猛地背转身去,掩面说:“妾面容老丑,羞对故人,就此别过。”
“二叔祖未见,只有大长公主一家和东宫父女。”
韦尚书摇摇头,一脸很受不了的表情白了李千里一眼,坐下来用朝食,一边娓娓道来:“吴国夫人姓崔,你今日看见的崔宫正便是吴国夫人的亲侄女、褚令渠的表妹,崔娘的父亲没有出仕,一辈子都是个处士,住在我家隔壁,褚令渠入西京应试,便住在崔家,褚令渠又与我姊夫相识,姊夫常至我家,也就把他介绍过来。那时三姊已归家,褚令渠住在隔壁,本也就想攀个高门,崔娘那时还太小,所以褚令渠便把脑筋动到三姊身上,以为她是小寡妇好勾搭,后来他跟姊夫都授官后,便时常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来,三姊本也不当回事,但是后来褚令渠竟与三姊说起姊夫与陛下的事,害三姊怕自己耽误姊夫的前途,也就想成全他……总之,说到底,公主会出生都是褚令渠挑拨离间搞出来的!然后又把她送到我这里……所以你说,他跟我有没有过节?”
“老师说的,可是故赵郡夫人吗?”李贞一现在的爵位是赵郡公,其妻自是赵郡夫人。
女皇被她一梗,清醒过来,见一旁还有主父,总不好说是因他们婚事不悦,只随便扯了一事,却见韦夫人诚惶诚恐地连连叩首:“拙夫执拗,妾本以为他入朝会收敛些,却不想天下竟有这般不知进退的男子……”
“李相公几时偕新夫人来我宅中?”公主冷不防从旁插过话来,笑靥如花:“我们太师母徒孙,也好亲近一番。”
“呵呵,真有你的,到时候就这么说。”
这……李千里与韦尚书快速地对看一眼,韦尚书那日过堂便见过萧玉环,根本没注意她,只知道有这么个宗女而已,却没想到她就是持盈郡主。而且……韦尚书与李千里又快速地瞄了瞄对方,从萧玉环……呃,现在要叫萧玉瑶了,从萧玉瑶的话里,透露出她早就注意到了李千里,难怪上次女皇说持盈郡主说了非李千里不嫁……师生两人暗地抖了一下,这下糟糕,只希望这不是萧玉瑶的初恋,年轻女孩的初恋最盲目最执着,他们又同时看了看面上漠然的李贞一,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就是李贞一被喜欢了快五十年……
“此是持盈郡主。”女皇淡漠地说。
但是,当这种自结的亲属关系缔结成盘根错结的人情网,当初文皇帝立国时特地选战俘为内侍、以断绝亲族干涉的立意,便不存在了。李千里看着那老妇,她的衣衫虽不奢华,却看得出来是上好的质料,而且是正绯色,想必她应是尚宫等级的内命妇,这么高的身份,却不知她为何离京?而她的三个养子拜窦文场为父,想必是她牵的线,也可猜测她跟窦文场关系不浅,尚宫是最高品阶的内廷女官,与内廷最高阶的内侍结为干亲家,又有何人能敌此二人?
人都还没死,连孝子都讲出来了……李千里心想,他束好腰带,扶正帕头,想了想,低声问:“呃……学生一直想问,主父与老师从前有什么过节吗?”
韦尚书胸有成竹,呵呵笑着说:“问题在于不是秋霜娶璇玑,是秋霜嫁给她,所以从律令上说,秋霜是虞氏妇了。”
“阿母不可啊……”、“阿母……”
“身为属官,他是个冷血没心肝,除了外表外一无可取的人。”李千里毫不犹豫地说,吸了口气,又说:“不过现在坐在御史大夫的位置上,能在朝堂上坚持己见又不伤人和,御史台至今也只有这一位了。”
韦尚书放下东西,一整仪容,便出得门去,众宫人内侍见他出来,连忙拜下,齐声说:“相公万福。”
好像只眨了眨眼就天亮了,外头一阵人声,夹杂着女人的啜泣声,李千里m.hetushu.com.com缓缓起身,盘膝坐直,这几日赶路疲倦,只觉得心头竟一阵烦闷,便顺手从胸膛中间的膻中穴循心包经经天泉天池曲池等穴,一路按到左手中指的中冲穴,如此再三,直到心跳平稳,方才起身用手巾兑了些水擦擦脸,出门查看。
“嗯……算有……吧?”李千里从没听韦尚书讲过这么多秘辛,不过听起来怎么跟坊间那种三流传奇一样?他默默捧起茶碗喝了一口:“不过事情哪有那么刚好的?又不是传奇故事……”
“喔?到这时才来,翅膀断了,用爬的吗?”上皇无关痛痒地斥了一声,稍一动头,指着李韦师生二人:“千唷,你老师是碗温吞水,你这年轻人,手好脚好的,怎不早点入京来?到哪下蛋去了!”
女皇张口欲言,却听李贞一淡淡提示:“臣启陛下,中书令与虞里行的婚姻,虞里行应为女户 ,而中书令以赘婿入户。依《梁律疏议》,赘婿是否携财入户皆由双方议定,若妇死则子女继财,无子女亲眷才得以赘婿继产,除此之外,并未进一步规定赘婿是否在律令上视同正常女夫,纳婿妇人亦未明定是否与正常妇人同。且虞里行为官人,《梁律疏议》、《六部式》并《梁六典》内只言官人|妻,而未言官人婿,法不溯往,即令此时明定女官夫婿之份,亦不得溯及中书令与虞里行。故,此婚可说是中书令入为虞氏赘婿,亦可为虞里行娶妇陇西李氏,换言之,李虞合婚之事,与陛下国婚略同,乃互为内外之姻。”
“是。”
“你、温杞跟王氏不是也是这样?跟璇玑不是也这样?”韦尚书毫不留情地一口气说完,顺口咬断腌瓜。
“我若是离开朝廷,璇玑马上就会被贬出西京,一辈子在岭外不得翻身。”
出得二门外,只见约莫五六十名鬓已星星的中年、老年妇人,正向着皇城方向辞拜,因为一出长乐驿,就不是西京地界了,旁边几个中使则在安排车驾。又见外面马蹄声响,十余骑京马奔来,却是十余名中年内侍飞奔而入,妇人中便有人起身迎向,这十余名内侍或与年纪轻些的中年妇人抱头痛哭,或跪地哭拜老妇,哀声四起,听了令人鼻酸。
“关你什么事!”女皇气得口不择言。
他在心里深深地叹着气,他已经无力去解这段冤孽,也早就放弃挣扎,只要儿孙好,就够了……他气若游丝地唤了一声:“崔尚书……”
“是啊,但愿如此吧,不过陛下欣赏专一的男人,越是专情越是不驯,她越舍不得放走,你就放心吧。”
那妇人看起来气度高华,摇着头说:“阿姐任女史多年,多少有积蓄,再说往东都剃度便入空门,又有何处能使钱?倒是你才刚有品阶,往后娶妇、养儿都还需用钱,还是留着吧……”
韦尚书兀自絮絮叨叨,李千里知道座师大人只是不喜欢旁边有人却没声音,所以总是云天雾地啰唆着,两人一前一后来到紫兰殿外请见,不久就有宫人引他们进去。
女皇眸光一动,瞥向李贞一与公主,却见他们脸色深沉,再看倚在一旁凭几边的上皇和韦尚书,倒是一派轻松,便知道在上皇党中亦有两派说法,她回头看了主父一眼,沉声说:“玉瑶,来见过元辅。”
早晨的紫兰殿内,主父背靠着数个枕头,半坐在榻上,宫人正在喂药,他的视线已是模糊,手脚也因为风痹麻木不能动,只有耳朵还好使。他听见外面一阵走动交谈,知道上皇、女皇、太子、公主、持盈郡主、太师、大长公主、前中书令、李贞一等人都在,他们在讨论着当前的国事,隔着帐幕,一如以往,他感觉十分孤单。
“禀上皇,臣于本月十日,在东都与监察御史里行虞璇玑结为连理,未及置酒宴请同僚,过几日备得水酒,还请上皇玉趾亲降寒舍,再请上皇做个现成媒。”李千里横竖是豁出去了,不太习惯地挤出一脸笑意,以示新婚之喜。
“朕要宰了他!朕要宰了他!”
女皇与主父、太子也都震惊得说不出话,却听上皇抚掌大笑:“呵呵,好啊好啊,五姓算什么鸟?没有一个你还有千千万万个姓李的,到底是婆娘重要啊,是不是啊?”
一路上,凭着韦尚书那身紫团花绫袍与李千里的浓紫凤池纹绫袍,师生二人完全没受到阻拦,而且顺利探问到紫兰殿里的状况,当然也免不了看见几个小内侍一溜烟奔去报信。
他与韦夫人的事,如女皇与李贞一一般复杂,并不只是韦尚书与李千里说的那样全是他一人的问题。今天,四个人里,一个已死、一个将亡,李贞一的眼目却一直在韦夫人身上,而女皇失去他后,可能会觉得轻松了吧?主父在心底苦笑,其实他跟女皇的相处,就与一般宦门夫妻一样,儿女长成后,夫妻就像同居共爨的家族人一样,各有爱宠也不稀奇,本来他们不会这么痛苦的。
“直接跟陛下说我已经嫁给璇玑,不能嫁做皇夫。”李千里说。
“宝宝!不行!”
“如何如何?不涩不柴吧?”韦尚书期待地问,根本不待李千里回答,又得意地捻着胡须摇头晃脑:“这可是从王司马《秘要》中抄出来的方子,哎呀,端得是香气亭和、牙齿光洁,真真好用啊……”
“牛刺史顺利离开深州城,目下正在刘护军营内。冀帅攻破深州,据说深州城内已无人迹。魏帅自认无力控制魏镇,已立都知兵马使为留后,现在正要前来西京请辞魏帅。淮西镇未拉拢魏镇,所以淄青也没有加入战局,眼下武宁镇已与叛军打起来了,武宁节帅尚未求援,应当还在控制之内,所以淮西也没有进一步动作。”李千里回答。
这一头两三个内侍跪在一老妇身前,其中一人抱着她的腿大哭:“阿母……儿不忍去阿母……儿与阿母去东都罢……”
“此是韦相公并中书令李相公车驾。”外面燕寒云回答。
李千里默默往后退入正堂,他一直不太理会内廷的势力,因为窦文场还听女皇的话,不过从河北神策军与东都含嘉仓的事看来,窦文场手下似乎也分了几派出来,现在他在世自然好,若是他压不住了,又或者主父死后,宫中势力有变了,到那时,内廷与外朝只m•hetushu•com•com怕免不得要有冲突……
李千里直起身,以答问之姿回答:“臣驽钝,请陛下示下。”
“主父是唤崔宫正吗?”宫人问,他点点头,这个宫人的声音很陌生,她轻声说:“崔宫正这几日身子不爽,在掖庭宫养病。”
李千里还来不及回答,公主话音一落,李贞一随即说:“师徒如父子,她还是你的下属,你当真不怕舆论攻讦吗?”
“除了这四个字,你没有别的话好说了吗?”
“阿姐此去,不知何时能见,这是弟一份心意,阿姐带着随时花用。”一个内侍从背上取下一个包袱,塞到一个约莫四十余岁的妇人手中。
李千里与韦尚书虽不常出入此处,但是也都知道禁苑本来就有查核,所以拿出鱼袋里的鱼符递出去,接着就顺利通过了。车驾直入玄武门,入门后在翰林院外下车,这才悠哉地安步当车往紫兰殿去。
于是公主扶上皇先行,其余人等随后,韦尚书经过李千里身边时,拍了拍他肩膀。众人鱼贯而入,其他人因为一直都在殿内,便无须行礼,李千里似乎瞄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不暇细想,便与韦尚书深揖拱手为礼:“臣吏部尚书韦/中书令李,伏望陛下万福金安。”
“老师……我只祝你和璇玑姊姊,白头偕老……”而今,萧玉环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女皇迟钝地看向孙女,她自幼就与女皇长得很像,侧面尤其相似,萧玉环低低地说:“我喜欢璇玑姊姊,也喜欢你,虽然你们加在一起,我不能双倍喜欢,甚至很是难受,但是我不愿意看你们不快乐……璇玑姊姊的朋友寄兰姊姊常说,女人要有女人的义气,我想,祝你们幸福,应该是女人的义气吧……”
三海池上吹来一阵凉风,一艘龙首大舟泊在远处,韦尚书望着大舟,随意地问李千里:“秋霜哪,你觉得我姊夫是个怎样的人?”
“崔娘……”韦尚书似乎很感慨地叹了口气,柔声说:“你我自幼比邻而居,令兄令弟与我亦是文友,可惜他们都已谢世,童蒙之友,至今只有你我,昔日垂髫今时白发,何耻之有?”
“听闻元辅曾往东都持盈观欲见,其时,我已入西京,于持盈观内假充者,为三妹西真郡主玉婉,若有得罪之处,还望元辅见谅。”持盈郡主低声说,李千里有些错愕地瞪着持盈郡主,谦辞后才听她说:“我不顾皇祖父苦心栽培,逃出东都往西京游玩已有数年,一直避于女尚书崔氏私第,崔尚书第与御史台公田相去不远,曾见元辅至公田教授诗书,尝于窗下听书,心中甚是感佩,故以幼时玩伴已故宗女萧玉环之名报考乡试、进士试,方得为元辅门生。这一向欺瞒座师,实有难言之隐,还望元辅海涵。”
“陛下若逼你跟璇玑义绝呢?”
韦尚书摇摇头,自与其他识得的宫人作别,又与内侍们见礼,探问几句宫中事才回房换上袍服。
“慢慢慢!家内?你哪来的老婆?”上皇一口截断他的话头,其余人等自然也都听出了家内二字,李贞一看了李千里一眼,又看向韦尚书,对上小舅子笑嘻嘻的表情,脸上一沉,却不说话。
“正与持盈、大长公主等在内殿。”公主回答。
李千里听到这两句,左脸微微抽|动,似乎要讲什么,又吞了下去,低头看了看手上紫玉环,表情才松开来,郑重地说:“倩娘与温杞之间什么都没有,她不是个朝秦暮楚的人。”
女皇虽然君临天下,但是好洁爱净的女子本性是不改的,她的近臣都必须口齿芬芳、身衣清香,曾有某举朝知名的才子,自认相貌潇洒、才华不凡,却一直未入翰林之列,更不曾亲近天颜,于是多方打听,这才知道是他患有齿疾,有一回奏事时被女皇闻到他的口臭,从此不列入近臣考虑名单。
她忍了许多年,每每咬牙咬得牙龈酸疼,恨得咬出血来,血的腥味漾在口里,胸膛里的愤恨与不平却都爆发出来,她几乎要挣脱主父,扑上去杀了李贞一,但是那时,殿外传来人声,说是韦夫人求见陛下。而她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相貌中等、看来已不年轻的女人走进,向她行大礼,低声说:“贱妾韦氏,听闻拙夫干犯陛下天威,都是贱妾无能,未替拙夫设想周全,礼节有亏,请陛下治罪。”
昨夜梦里,他梦见了三十年前去世的亡母吴国夫人,她就站在榻边,一夜无言,脸上表情却不欢喜。前一天夜中,他梦见赵郡夫人韦氏,她与她二十余岁便亡故的杜氏女儿,并肩坐在韦家后院里做针黹,她们没有抬头看他一眼,而他也只是无言地看着她们,一如当年他隔着小院女墙,凝视着她们,只是那时杜氏还很小。
李千里身子不动,眼睛微眯,却听右方有衣裙摩擦的声音,一人走到他身前跪下,长揖道:“东宫不肖子,拜见元辅。”
“废话,当然是赵郡夫人。”
女皇听完李贞一的话,便知道这桩婚事在法理上完全成立,对于那个禁令也可低空飞过,并不算完全违反不立正室的约定,因为大不了就是虞璇玑不受郡夫人封,换李千里将来在官衔上多加一个县君乡君郡君罢了。
女皇想到自己被李千里摆了一道,简直咬碎银牙,她抓着衣袖,猛捶了床榻一下,她是个娇小老妇,站起来也不过高李千里半个头,声音却大得吓人,她戟指怒声喝问:“元辅,你答应过朕不立正妻,此时却欲以赘婿为借口逃避此约吗?就算法理上你没有违反约定,但是事实上你为了娶妻,将朕的特典殊恩视为粪土目为枷锁,虽无犯行已有犯心,实实可恨!还有驸马!你身在东都不可能不知此事,你身为座师竟不拦阻,朕对你失望透顶!元辅!你若立时写下和离书,朕就将此事揭过不提,若不然,朕必问你欺君之罪!宦途性命,皆在你一念之间!”
只是明知感情不能比较,他和女皇却都忍不住与李韦夫妻比较了,他恨女皇不像韦夫人,女皇也怨他不如李贞一,李贞一与韦夫人的婚姻只有两个人,而他与女皇的婚姻里塞了四个人,再深的感情也会消磨殆尽,更何况他与女皇还不只是夫妻、更是君臣。
“禀太子,下官于本月十日,在东都与监察御史里行虞璇玑结为夫www.hetushu.com•com妇。”李千里流畅地回答,殿内一阵死寂,主父昏聩的眸子一闪,却没有说话,李千里淡淡地说:“行礼匆忙,未得置酒宴请西京同僚,过一阵子补请喜酒,还请太子赏光驾临寒舍。”
“啧……你在紧张吧?”
“但愿如此……”
“唉……男婚女嫁天经地义,东宫王待诏早有家室,以谭主簿为妇,尚有东宫主婚,也没人敢说什么,更何况秋霜璇玑都无家累,有何处可攻讦?”韦尚书又跳出来护驾。
崔宫正长叹一声,放下手却依然背着身,低声说:“妾十六入宫六十出,阿兄阿弟因事谪死岭南,家门零落,有何颜面与相公论交?妾以衣冠女入宫侍君,便以陛下为天,相公是陛下儿婿,自是主人,岂有主家与仆臣叙友之理?”
那老妇脸色一变,扬起手来一人一个耳光,厉声说:“混帐!内侍宫人侍君方是本分,你兄弟三人是窦中尉养子,怎得往东都侍奉一将死老妪?大郎怎能领二弟作此儿女态?若要报我养育之恩,应效当年高公挣个国公,将来以国夫人赠我泉路才是!休要再提调东都事,若于东都见得你兄弟三人,我立时碰死!”
“那半璧江山暂且无忧了……”上皇低声说,与李贞一交换了个眼神,便说:“唷,阿千哪,想不到你还挺有手腕的嘛,能把关东那几只恶鸟哄得这般安分,我倒要好好奖赏你了。”
“那我就辞官不干,回家奶孩子。”李千里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说。
“为什么不能!昭阳有你就够了!”……
“平王相王亦在其中?”
“说来也是我害了她,若不是我轻忽家事,温杞也不至于纠缠倩娘,而后也就不会有阿巽的事……”
见礼罢,韦尚书便问:“怎地不见陛下与东宫?”
“不行,你要想想昭阳,你不能杀掉昭阳的生父啊……”
“阿兄说得是。”、“儿与阿兄阿弟等这就请调。”另外两人随声附和。
韦尚书将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散步着,远远地可以看见含凉殿的屋脊与殿外整片的柳树。而紫兰殿位在三海池北,距离玄武门不过半里远,向来不是妃嫔居住之地,而是皇帝自禁苑射猎后稍事休息的地方,因此甚是朴素,距离外朝也很远,但是玄武门内外动静,紫兰殿都能听得见,女皇选此为主父起居所,可说颇具深意。
“刚刚不是才把回家奶孩子说得挺有气势的?连我都被你唬过了呢!”虽是这么说,韦尚书还是一脸完全没有被唬过的表情。
李千里伏拜在地,萧玉环在一旁听着他叙述对虞璇玑的心意,说来说去,他宁愿领罪也不愿和离,萧玉环只觉得日月无光,她自然早早就打听过他的事,知道他是个从考试就汲汲营营想往上爬的人,连死了女儿跑了老婆都不能阻挡他做官,但是此时,他为了虞璇玑竟毫不犹豫地领罪,那她还有什么指望?
女皇气得五官错位,声音也不自觉地拉高,八幅宽的黄裙就在李千里身前数寸烦躁地扫来扫去,他只觉得一阵压迫感从上而来,但是若此时疲软下去,就前功尽弃后途无光,所以他直起身子,深深伏拜:“臣自家内及笄,便心系于她,十余载风风雨雨,此心未改此情愈坚,至河北事发,臣与家内分隔两地,臣有首辅之责、家国之托,不得不将其遣入魏博虎狼之地,自居东都,本欲压抑情思,以图陛下谅解再行成婚。然河北事瞬息万变,当此生死交关之际,愈增思念爱慕之情,待得相见之时,一刻不及稍待,遂定鸳盟。至河北事平,臣偕家内归返东都,尽述往事,更不忍分离,便恳求恩师允婚,恩师基于爱护之心并故人之情,勉为其难应允此事。此事过错全在臣一人身上,家内成婚前并不知臣与陛下有约、恩师更是为臣所累,臣确有欺君之心,请陛下降罪。”
“公主此言,臣不敢受,倒是臣久疏问候,还望公主海涵。”李千里郑重地拱手说,毕竟公主一来是他的师母、二来是皇亲,虽然中书令礼逾天下臣民,但是人情并不允许他托大。
堂堂五姓出身的中书令兼御史大夫去做赘婿,实在不可思议至极!
李千里却不领情,不无怨念地说:“微臣倒要多谢上皇那次胡言乱语,使璇玑养成谣言不入耳的习惯哪。”
若说刚刚众人只是心底惊呼,此时忍不住都抽了口气,虽说律令上赘婿与一般夫婿的权利并未有别,但是在梁国社会普遍觉得,只有穷得活不下去或者没有自立能力的男人才会去做赘婿,就是虞璇玑的姊夫,在外头也决口不提他是赘婿,此事也只双方亲戚隐约知道而已。
“朕年事已高,恐儿孙不肖,欲将儿孙托付元辅佐治天下。元辅,国之栋梁,又当年富力强,必不负所托。皇夫此际需得静养,元辅若应承此事,皇夫也就心安了,说来是朕与皇夫有些儿女牵挂,倒叫元辅见笑了。”女皇异常和蔼客气,右手握着主父,十分诚恳地说。
韦尚书命他们起身,走到那老妇身前,拱手说:“崔娘怎得在此?”
“持盈已至?”
“郡主万福。”李千里拱手为礼,基于礼貌,位极人臣的中书令只需对亲王公主以上皇亲稍事臣礼,以下则依年龄行平礼或半礼,持盈郡主年纪比他小,自是半礼即可。只是郡主的声音一入耳,却熟悉又觉异常,等到郡主抬起脸与李千里一相,他瞪大眼睛,只咬住舌头没有出声:“……”
上皇眉头一动,扫向李贞一:“怎么样?我就说天下最难的,就是干这种押人入洞房的事,这下好了,老婆都娶了,这几日只怕也在孵蛋了,你就好心些,贵手高抬,放过人家小夫妻,收起你那死人脸,说句恭喜你琵琶别抱梅开二度,祝你双宿双飞燕燕于飞六畜兴旺五鬼运财不好吗?”
韦尚书闻言以袖掩口偷笑,其余人等则都是一怔,正待详问,却听一内侍奔来:“陛下请上皇、公主、国老与诸相公至内殿相见。”
韦尚书见他又提起当年,连忙又把话截断:“旧事已过,再提没有意思,死的死了,活的就好好活,你把这片歉疚报在璇玑身上,好好照顾她也就是了。倒是今日入宫,若遇上持盈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上皇所言极是。”李千里稍稍一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