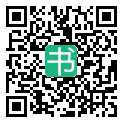第66章 鸾帷凤枕,记取同心结
宣太后不紧不慢地继续啜了两口茶,才转动凤眸,看了唐天霄一眼,“听说昨天她闯了祸,居然逃得无影无踪,连皇上都找不着?”
可浅媚却不解了,疑惑地望他半晌,实在看不出什么来,遂道:“不管你是不是吃干饭的,皇上是不是吃干饭的,总不能让无辜的人当替罪羊罢?何况……何况她不但是一品宫妃,也是……也是他的妻子之一。”
费尽心机,其实也无非想多分一星半点君王的宠爱。
御路两边又各设六方须弥座一个,座上立着重檐六角亭,亭身镌着姿态各异的寿字,却是为太后祈福所用。
仿若阳光凝作了一束,那样直直地贯到了唐天霄体内,立时让他通体温煦透亮,连常年灰蒙蒙的心头也似破开了一道缝,暖意融融。
她笑着,吩咐宫女搬了椅子在自己跟前坐了,目光却投向了依然垂着眼帘跪在下面的可浅媚。
可浅媚得意地摆弄着腰间的荷包,并不答话。
可浅媚脚步有点迟疑,不顾正行在大道之上,身后尚有宫人跟随着,便拿手轻轻碰了碰他的手指,低声问道:“天霄,太后会怎么处置我?”
可浅媚身上愈发觉得凉,慌忙将窗扇关了,然后倚在窗边,打开荷包。
这晚的睡梦里,她看到了记忆中那个风姿卓然目光温厚的男子身影。
唐天祺点头,道:“也是,你该懂的。我听人讲过你的事,你可不是宁清妩那样手无缚鸡之力的闺阁弱女。皇上若得你倾心相助,想来以后也不会常常不快活了!”
可浅媚看着那梳子,只觉十分眼熟,一时却记不起曾在哪里看到过。
她敲打着酸疼的腰从床上滑下时,才看到唐天霄已经穿戴整齐,负手站在窗前向外眺着碧天轻云,俊秀的面庞缥缈而安恬。
唐天祺噗地笑道:“怪不得皇上说你现在了不得,动辄就吃着干醋不让他好过,果然呢!”
宣太后笑道:“罢了,没长个儿已经这么大胆子了,等真的长高长壮了,是不是打算连哀家都拽下椅来打一顿?”
可浅媚想抬高嗓门,却反而压抑得低了:“你是说……我连累了她?”
唐天霄低了头,将她腰间的长鞭解下,收到自己袖中,才说道,“记住了,德寿宫不是熹庆宫,若你敢连这里也闹起来,朕也不会护着你了!”
简单得就像唐天霄用两人的头发编成的同心结。
他的面庞便在她的掌心下柔软,她甚至感觉得到他温柔的笑纹有掌下轻轻扬起。
唐天霄便哭笑不得,也不忍心吓唬她,低低安慰道:“别怕,没大事儿。到底你只是打了几个宫人,又没打皇后,呆会你只需乖乖认了大闹熹庆宫的罪过,血燕的事由朕来说。到时便是真罚,应该也重不到哪里去。了不得打上十杖二十杖的,扔你到冷宫呆上几天。等太后性子下去,皇后那里病情好转了,朕自然接你出来。”
可浅媚心思玲珑,一眼瞥见她身侧侍立的贵夫人面上浮着讥嘲笑意,虽不认得是沈皇后之母,却也知必被人提前告了状了,忙叩首说道:“浅媚不敢!浅媚年少无知,平日只在瑶华宫里侍奉皇上,其他万事不知,万事不理,忽被皇后召去,口口声声说浅媚害了龙嗣,又不容浅媚辩解,遣了卑贱宫人便向浅媚动手。浅媚怕被她活生生打死,这才打开那些下人逃了出来,等候皇上为我作主。”
可浅媚只着了罗袜,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踮起足,双手蒙上他的眼睛。
可浅媚见门扇关上,取了荷包,在手中轻轻地抛着,接着,轻笑着和着自己的动作念道:“想得起,想不起,想得起,想不起,想得起……”
只是唐天霄总是慵懒倦怠,眸间流转的光华,往往只为眼前的美人或美酒美食;而宣太后即便面庞上蕴着笑意,眸光亦是凌厉,仿佛如刀锋般一眼能切到人心。
既收揽了人心,又讨好了君王,顺便把最有威胁性的对手放到自己眼皮底下,也方便从旁监视,或就中取利。
可又似乎不是梦。
她抬眼望望天色,道:“这时候,太后该在午憩吧?”
有女人的地方,就有争宠。
便如此刻。
她受了那记窝心脚,后来又在山上受了重伤,便再没有去追问头发的下落。
越过一道横跨东西的莲池,德寿宫已赫然在目。
她口齿清晰伶俐,虽不高声,却人人听得清楚。
她曾截了一段自己的头发,又曾以一记窝心脚的代价,截下了他的一段头发。
这一次,可浅媚连耳朵根子都红了。
唐天霄的怒气并没能维持多久。
可浅媚面露不悦,扭头看着宫门前摇曳着的碧玉般的新荷不说话。
这座宫殿高建于青白石须弥座上,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四周俱有饰以飞凤腾龙的汉白玉栏板,丹陛左右分置日晷、嘉量、铜龟、铜鹤等物。
她撩动丝弦,在琴声泠泠里郁郁地说道:“你听过那支《薄媚》么?西子死了,沉于越溪……她爱的故国,用她殉了爱她的君王。”
“嗯?”
可浅媚拔下头上一根镶宝的金簪子,塞到嬷嬷怀里,说道:“还请嬷嬷多多费心,快快查出真凶来还我清白。一个人困在这屋子里,着实闷得很。”
可浅媚眼珠咕碌碌转了两下,上前便抱住他的腰,八爪鱼般蹭在他身上,笑道:“不喜欢你,才不喝你醋呢!”
心里忽然便踏实,仿佛走到哪里,都有他的目光远远相随。
“不让她认下,难道让你认下?”
爱或恨,有了抉择,也便轻松了。
唐天祺急急应了一声,待要离开,又扶了窗棂向她叮嘱,“记好了,别惹事,别逞匹夫之勇。你身手再好,皇宫也不是你逞匹夫之勇的地方。估计再熬个一两天的,皇上就可以把你接出去了!”
内侍松了口气,到底低声答道:“禀淑妃,是贤妃娘娘在那边房中哭着呢!”
他将她牵在手里,与她并肩走着,绿绒绒的草地被踩得悉hetushu.com.com悉碎响,他沉重的叹息,似把她的心也踩到了脚下,那样悉悉地碎响着。
无论是北赫王宫,还是大周皇宫。
她披了衣,推开窗扇时,那厢立刻有守着的内侍跑过来,警惕地望向她。
即便行走在闹市之中,若人们不留意到袖口似隐似现的金线蟠龙,也只会把他当作出身书香门第的贵家公子,风流雅措有余,沉雄豪宕不足。
可浅媚抿着唇嘿然道:“大周皇帝才是独一无二的,再无他人能及。我什么时候怄你了?我又怎么敢怄你?”
何况身畔还有从人,又询问着这些随时可能要人性命的宫中秘案,哪里敢收这等公然贿赂?
她便仰起头,向他许诺:“七叔,我帮你,我帮母后。何况,我也想去中原。”
她真的听到了女子隐约的哭泣。
幽细,悲伤,委屈,心给揉碎了般疼痛的哭泣,听来有几分耳熟。
光泽幽幽下,绣了连理枝,比翼鸟,翠叶朱翼,极是灵秀隽妙。
唐天霄轻笑,“我自是早就预备好哄你了,所以当时便藏了起来。不只藏了这个呢!我还留了一件东西哄你。”
唐天霄叹道:“浅媚性情纯良,又是异邦之人,宫中并无心腹之人,哪里懂得那些药材配伍害人之道?落胎之事,且容慢慢清查,若真与浅媚有关,朕也绝不姑息。”
只不过,若一梳梳到白头偕老的梳子都是妄言,若亲手编的同心结发都是梦想,这世间所谓的真情,未必太过无趣。
听说要挨打,可浅媚便觉得背上有点痒,右手不自觉地便摸向腰间的长鞭。
可浅媚点头,“其实你是想挽回的,只是挽回不了而已!”
心里隐隐在抽痛时,她却扬一扬唇,自信地笑了起来。
那日清晨,唐天霄亲自领了她自怡清宫出来,却是许多宫人都瞧见的,不问可知,他们当晚是同宿于怡清宫了。
可浅媚怔了怔,忽然便也怒了,一甩手说道:“和你开玩笑也不许吗?好,我不提她,有本事你自己心里也别提她!”
内侍显然早已得过吩咐,远远地避在一边,直到这时才又回到房门前守着,拿出一副尽忠职守的模样。
“把血燕送给宇文贵妃大约是什么时候也一点都想不起来吗?”
“谁心里提她了?”
可浅媚猛地坐起,推开不知什么时候蒙到自己脸上的锦被,擦一擦额上的汗水,重重地吐了口气。
喜欢不喜欢,其实很简单。
“这就是……你那位淑妃?给你找出来了?”
唐天霄恼得想拿针线来缝了她的嘴,恨恨道:“就见你一天到晚伶牙俐齿,有事没事便来尖刺我两句!却不知你自己背地里又是怎样的。那陪你看日出舞长鞭的美少年,也不知有没有拉拉小手亲亲小嘴什么的,偏偏还不断喝我的干醋!”
可浅媚睁大眼望向他时,他已低下头,解下腰间素常佩的荷包,递给她。
“什么习俗?”
她的唇动了动,低声道:“你什么时候去把这梳子找回来预备留着好哄我的?”
庑房外虽有人守着,但屋中收拾得倒还整洁,卧具茶具等物都是她进来后宫女才抱进来的,一色俱是崭新的。
此时听宣太后问起,可浅媚不敢怠慢,垂着眼帘低了声音答道:“是,臣妾便是可浅媚。”
唐天祺点头:“嗯,她不是你眼中钉,只是你是她眼中钉,也是其他后妃眼中钉。你不拔她们,她们早晚来拔你。不信你试试,若你有一天失了宠,看看会有多少曾经对你笑脸相迎的宫妃毫不犹豫把你踩到脚底下。”
可浅媚愁眉苦脸道:“皇上若开心起来,三天两天赐下东西给我,我不过当时看一眼,吃的用的全是宫里的份例,贤妃姐姐给安排得好好的,哪里还管这些事?听说旁的宫里都有宫女专司这些事务,可跟我进宫的侍女连中原话都不会说,想管也无从管起。我又不是做生意的,难道叫我天天拿支笔来记每日进了多少东西出了多少银子?”
“什么东西?”
仿佛有越溪冷冷的溪水漫天涌上,堵上她的口鼻,她失声惊叫,却在惊叫时听到了女子心碎的哭泣。
可浅媚闻言,哼了一声,砰地关上窗户,果然再不出声了。
“哦……哦……”
唐天霄没有答话,却从怀中掏出一枚样式甚是寻常的桃木梳子,捉过她的手,放到她掌心。
可他临别时那般无奈而担忧地望着她,叮嘱她不许闯祸……
内侍不敢回答。
只因它根本没想到,主人其实只把它当作了一条狗。
他悠悠地向她叹息:“若势不可为,我宁愿你过得开心些。”
但沈度大将军是朝中手握重兵的将领之一,沈夫人又是宣太后的堂妹,素受尊崇;周帝与沈皇后又是帝后情深,偶有在跟前提及沈后一句半句不是的,立刻被责罚了远远打发了去。久而久之,谁又敢在唐天霄或宣太后跟前说他们半句不是?
不过,即便是全部了,大约也不妨事吧?
唐天祺摘了一朵牡丹,慢慢地在手中捻着,低声叹道:“谋害龙嗣的罪过,总得有个人认下吧?”
可浅媚心头突突直跳,低头玩着荷包,飞快转过话题:“你是吃干饭的么?”
“我的兵马么……”
巳时正,唐天霄带着可浅媚前往德寿宫。
“你不只是成安侯吧?你手里不也有很多兵马吗?全是干饭的?”
内侍答道:“这个……奴婢不知。”
傍晚时分有太后宫中管事的嬷嬷过来,细细询问当日血燕之事。
唐天霄从身后拥住她,轻轻叹息:“你是独一无二的,再无他人可比。别再疑我,别再怄我,好不好?”
他叙说时声线很和缓,而可浅媚静静地听着,托着掌心那把梳子,竟似看得痴了。
见内侍自觉地走到稍远处,唐天祺才压了声音笑道:“是皇上叫我来看看你呢!”
可她知道的还不如嬷嬷事先查到的消息多。
唐天霄完全失语,只m•hetushu•com.com觉身体给她蹭得阵阵发紧,只得拥了她笑骂道:“你这小妖精!我怎么就遇着你这种怪物了?”
那一刻,她摸向腰间长鞭的手抓了个空,却抓着了晨间被她抢过来的荷包。
她的心口忽然剧烈地跳起来,鼓点般咚咚敲着,堪堪要迸出胸腔。
可浅媚低头道:“那恐怕是宫中之人以讹传讹误会皇后了。怎么许多宫人都劝我小心,说皇后娘娘手段厉害,当年宁淑妃受宠,她叫进熹庆宫一顿棍子下去,差点命丧当场。又道宇文贵妃怀了龙种,皇后娘娘后位不稳,这笑里藏刀的,不知在打什么主意呢!”
唐天霄叹气。
可浅媚哂笑:“踩我?唐二哥认为我会惧怕这样的小人?”
记住了,不许闯祸。
谁若这时候不睡觉,总是惹人疑心,何况还是个身负武艺的异邦女子。
如果他只是把她当作了更珍贵的一匹马或一条狗,他本没必要这般讨好她。
她喃喃道,“沈家就是再厉害,难道连你这个大周天子也怕了?”
可浅媚脸一红,道:“谁吃他醋了?只是皇后受了惊吓,他们帝后情深,自是要去看望的。不晓得有没有多陪陪宇文贵妃?那位也病得不轻呢!”
哪怕身陷囹圄,哪怕前途莫测,只要他真的待她好,真心将她护翼在自己身后,一切必将迎刃而解。
唐天霄侧身笑道:“她闯了祸,也害怕得很,自然不敢回瑶华宫,却早就遣人告知儿臣了,并无逃走之意。”
赢得帝王宠爱,本是她来到中原的目的之一,但并不是她的目的的全部。
它一定没想到,危急之时,主人也会毫不犹豫拿它去换更值得保护的人或物。
可浅媚闻言,抿唇望向唐天霄。
玩得烦腻了,她望向窗外,月牙般向上弯起的明眸闪过讥嘲和不屑,低低道:“我想得起想不起,为何又要告诉你们?”
可浅媚心下一寒,问道:“那你认为呢?”
将同心结握在手中,她托着腮,已是烦恼。
可浅媚瞪着他,伸手便到腰间摸长鞭。
杜贤妃算不上多贤惠,也许也算不上多好的女人。
推开窗户时,便有芭蕉的阴凉绿意和着大片阳光悠悠荡入,阶下植着各色牡丹,此时正当盛放时节,姚黄魏紫,凝霞散锦,各竞风流,华美多姿,馥郁的香气袭来,连衣带都似沾了挥之不去的芳香。
柔软黑亮的头发所编,样式很简单,下端用缀了玛瑙珠的红丝带束住。
不知什么时候起,若无第三人在场,他与她像寻常夫妻一样直呼彼此名讳,你我相称。他固然诸多纵容,而她也没了最初对他的敬惧之心了。
她伏在窗棂上,很想一跳便跳出去,纵然还在囚笼里,到底不再是这样方寸之地的囚笼,连探手摘支牡丹都没法,更别说到外面探探,问一问这会子唐天霄去了哪里,猜一猜他晚上会不会过来。
月上中天,虫鸣啾啾,正是半夜时分。
只要他的眼睛里只有她,她的眼睛里,不妨也只容着他。
是因为那是他的嘱咐么?
“喂,别再打甚么馊主意!”
可浅媚压着嗓子,用轻柔温软的声线慢慢地答:“天霄,我是清妩。”
抚摸了半晌,她叹道:“我不吃醋。他有后宫三千,那许多的醋,我吃得过来么?”
德寿宫正殿内,有谈笑声正隐隐传出;等得了通禀,里面才没了声息。
加之当日平定康侯时他立过大功,宣太后和唐天霄俱是另眼相待,因此常在宫中走动。
其实他不像帝王,更像随心所欲的江南文士,兴至则对月饮酒,情来则携美花下……那样逍遥快活的日子,更胜神仙。
嬷嬷动了动唇,干笑着接了过去,转头带着小宫女匆匆离去。
唐天祺盯着手里被摘得只剩了花蕊的牡丹,自嘲道,“也差不多是吃干饭的了……”
只是显得她天真蠢笨,白白长了副好皮囊而已。
唐天霄忍不住呻|吟:“喂,丫头,你以为天下有几个女人有你这样的胆子,新婚之夜跑来割我头发?”
唐天霄皱眉提醒她:“那是朕的母后。便是她要打朕这个皇帝,朕也只能乖乖领杖,不敢说半个不字。”
她不晓得杜贤妃那里又有多少可以问的,几乎每次进去,都要有个四五个时辰,连午膳晚膳都不得安宁。
他只能沉吟着继续道:“浅媚年纪尚小,再隔两年或许会高大壮实些。”
她这么想着,手指便似渐渐回过暖意来。
唐天祺拿指头叩着窗棂,促狭笑道:“看着,看着,这还不是吃醋呢,连宇文贵妃的醋都吃上了!”
这日午后,她正在榻上假寐,忽听门前似有人低声交谈,忙推了窗往外看时,便见到了唐天祺笑嘻嘻的面庞。
唐天霄沉静地望着她,慢慢道:“中原还有个习俗,只怕你不知道。”
有权势的地方,就有争斗;
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
他慢悠悠说着,忽然望向她,苦笑道:“我和你说这些……丫头,你懂么?”
唐天霄微笑道:“这个同心结打得还好看吗?我以前看人家打过结子,不知多少的花样,可我只记得这一种,打了十多次,才打成这样。问靳七,说还挺漂亮的。你说呢?”
高兴时便去逗引爱惜一番,以让它更好地供以驱驰,或更忠心地看家护院;不高兴时一脚踢在一边,它还得反思是哪里伺侯得不周到,连怨恨都不敢。
她也不掩饰自己的疑惑,继续向外张望着,顺便问内侍:“太后宫中哪里来的哭声?半夜三更的,把我都给吓醒了!”
仿佛有一团火苗自胸前蓦地窜出,腾着浓浓的烟雾让人透不过气。
他轻而清晰地吐了几个字:“天霄必不负你!”
他携了她的手,与她五指相扣,踏入德寿宫宫门。
荷包里的乌发细致地缠绵作一处,编得极是细致,依然能让人感觉得出那双主宰他人生死的手在编织时的诚意。
她料定血燕之事必是沈皇后所为,但屡次提起都和-图-书无人理会,反是一向待她甚好的杜贤妃受了牵累,大是不忿,冲口说了,心中也是后悔。
“新婚合衾后的第二天,新娘梳过的梳子都会保留下来。一直到很久很久很久之后,两个人老了,有一个人先去了,剩下的那位,会把成亲时的梳子折作两半,一半放入棺木,另一半留着,直到剩下的那位也去了,带了半把梳子和爱人归葬一处,这梳子,便算是一生完满了。”
“天霄,正说着你呢,可巧就来了。”
而那对花骨朵般的玛瑙珠子依然通透,幽幽莹莹,似两滴朱红色的泪珠。
——便是虚情假意,拿她和其他妃子并无二致地看待着,也没关系。
唐天霄苦笑:“我们在一起也有这么多日子了,你且自己说,私底下和我相处时,你有把我当皇帝么?我又和你拿过皇帝的势派来压过你么?”
唐天霄踏入殿中时,便见几个素得器重的重臣夫人伏于地间见礼,其中便有沈皇后的母亲沈夫人。
宣太后摇头,“不成。你满心里疼着淑妃,又宠着贵妃,皇后也是心坎上的,第一便失了公允,哪里查得出什么真相来?不如哀家来查,也可旁观者清。”
从什么时候起,她也开始和别的妃嫔一样也在冀盼着帝王的目光,不但盼着他每日每夜陪着自己,甚至盼着他每时每刻陪着自己。
可浅媚的掌心已经捏出汗来,低声道:“我倒不知道,沈家竟有这等厉害了!”
他暗自皱眉,不动声色地放开可浅媚的手,道了平身,这才向宣太后叩头请安。
她只一闪,便逃了开去,扬一扬唇角道:“是我的,你刚给我了。”
宣太后点头,端过茶盏慢慢地啜着茶,向唐天霄说道:“我总算晓得你为什么宠着这丫头了。长得果然和之前那个清妩丫头很是相像,只是个儿要矮些,这眼珠子也似太灵活了些,不如清妩温柔有礼。”
她只想做个活得长长久久的笨人而已。
“贤……贤妃?”
唐天霄虽有几个异母的兄弟姐妹,但不是早夭就是出嫁,算来唐天祺这个叔伯兄弟,已是和他最亲的了。
只是同心结上扣着的红丝带,在紧关门窗的屋子内显得暗昧不清,倒像是蜿蜒而下的一缕鲜血。
宣太后扭头吩咐:“先带淑妃到后面庑殿休息去。”
唐天霄咳了一声,无奈道,“那……一切便交予母后吧!”
她的声音极是脆朗,此时寂夜沉沉,只怕连关在别处的杜贤妃都听到了,一时竟止了哭泣。
她把同心结抓在手上,抚摸着那乌黑漆亮的发丝,两颗玛瑙珠滚在指间,鲜艳通透的色泽,像指间迸出的一双并蒂花骨朵。
唐天祺已忍不住,伸出手来想揪她耳朵,见她侧身避过,依旧一脸不驯,咬牙切齿般低低喝道:“好罢,你不听我的话,小心日后给人打折了腿,看你还犟不犟了!”
唐天霄还要说话时,宣太后放下茶盏,摆手道:“这事就这样吧!委屈可淑妃先在德寿宫住上几日,待查清无事,自然放归。血燕曾由杜贤妃经手,她也难脱嫌疑,所以哀家已经把她召来,如今也关在后殿。”
又做梦了。
许久,她问:“血燕之事,太后那里可曾查出眉目了?难不成打算关我一夏天?”
可浅媚眼圈便红了,扁了嘴瞪他,好一会儿才披了衣服,走到梳妆桌前梳发,再也不看他一眼了。
“漂……漂亮。”
若能绽开,必定妍丽芬芳,酿出一室清绝香气。
唐天霄无语,好一会儿才道:“罢了,你收着便收着,别弄丢了。”
可浅媚撇撇嘴,道:“他为什么自己不来?陪着他的好皇后么?”
“你刚说还留了件东西哄我,既是留着哄我的,自然是我的了,对不?”
不过是月白缎面的普通荷包,只是御用之物,做工总是精致。
第二日,玛瑙丝带不见了,桌上的她的头发,地上的他的头发,也一齐不见了。
她待可浅媚的好,只怕一大半出于自己的私心。
可浅媚忙接口道:“是,皇上教训得有理,浅媚知错了!愿听凭太后发落!”
在她还没懂得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她已学会仰望他,将他的每句话当作金科玉律,直到……遇到那个长得和她很是相像的女子。
可浅媚握紧拳,道:“为什么是她?”
可浅媚老实回答:“怕了。”
如今,却是整齐精致的一枚同心结落在掌中。
她还未及辩解,唐天霄已喝止道:“浅媚,朕就说你头脑简单,甚么人的话都信。凤仪素来贤惠,当日宁淑妃之事也另有因由,你只听那些小人搬弄是非,怪不得酿出这些祸事来!”
“是,儿臣以后必定好好管教于她,不许她恃宠生骄。”
可浅媚依然开着窗,握着荷包望向杜贤妃关押的屋子,只觉指尖阵阵地发冷,仿佛锦缎的面料上凝了层冰,油脂般腻在了手上。
内侍唬得忙道:“淑妃,太后娘娘一向睡得浅,千万低声,莫要扰了老人家睡眠。”
可浅媚入宫不久后也曾随诸妃一起过来向宣太后请安,但当时她尚未受宠,宣太后也未曾留心。
如今可浅媚只以下人之口置身事外般朗朗说出,沈夫人不由一身冷汗。
于是,那曾再三被唐天霄逾扬为“贤德”典范的杜贤妃,不时在屋子里痛哭失声。
可浅媚犹豫着点头,忽抬眸,瞳人如映了碧蓝天空的湖水般明洁干净。
否则,为什么大闹熹庆宫的是她,送血燕的是她,却不来苛问她,只揪着杜贤妃不放?
唐天祺将盛绽的牡丹花瓣一瓣一瓣地摘下,低头道:“你自己不也说过了?只怪她是文臣的女儿,而你是异邦的公主。你死了,自有定北王陈兵以待,坐镇边关,北赫的李太后再怎么心疼你,北赫的骁勇骑兵再多,也没法真的为你出头报仇;文臣的女儿么,更不必说了,古来就有那句话了,百无一用是书生。杜得盛……老了!”
唐天祺听她这话,倒似有点凄凉之意https://m.hetushu.com.com,不由怔了怔,才道:“你也不用多心。皇上虽没来这里,可心里也时时牵挂着你呢!昨晚叫了我一起喝酒,喝得多了,几次和我提你。听他口气,似极怕你在太后宫里再闹出点事来;可这两日你又偏生安静得很,他又在猜疑你是不是心里不痛快,怕你憋出病来。我看不过去,这才主动说代他来瞧你。”
她自己说出了口,也不由地抱了抱肩,仿佛这样阳光正好的初夏午后,也有不知从哪里钻出的森森寒意,针尖一样往肌肤里扎。
这话一出,连一再用清妩激怒他也成了用情太深的明证了。
唐天霄立时皱眉,陪笑道:“眼看母后生辰在即,怎好再让母后受这等琐事烦心?不如儿臣亲自来查吧!”
唐天霄柔声道:“去吧,母后素来公正,不会冤屈了谁。记住了,不许闯祸!”
二人正在交谈时,那边已有宫女奔过来,扬声道:“成安侯,太后醒了,正在问起你呢!”
可惜还是没能摸着鞭子,只摸着了那只装着同心结的荷包。
嬷嬷推拒着不敢接时,可浅媚又道:“这个是请嬷嬷去帮我预备点东西的。”
暮色渐起,她的唇边有笑,眸光却黯淡下来。
宣太后哼了一声,道:“血燕之事尚未了结,你倒打算这样糊涂过去了?那你怎么向宇文贵妃交待?又怎能担保日后不会再有毒害龙嗣之事?”
果然是两人在山中同寝的第二日,她曾用过的那一把。
可浅媚怒道:“谁把她当眼中钉了?”
可浅媚忙笑道:“你又胡说了。皇上九五之尊,天下在握,又怎会不快活?”
她委实不像她外表那般娇俏柔弱。幸亏先将她的长鞭取走,不然即便他嘱咐再嘱咐,也指不定会闹出些什么事来。
“你在打什么主意呢?”
她握紧手中的同心结,低低道:“唐天霄,你不许负我,不然,我绝不饶你!”
他竟悄悄地收拾起来,每日扣在腰间么?
——也许牺牲它所换得的,也未必有多重要,只是在主人心目中的地位,胜过了它而已。
可浅媚继续道:“其实宫里谁不知道哪位娘娘最想着害了他人龙嗣呢!换了我,五年下不出个蛋来,也早着急了!如果换了她是文臣的女儿,或者异邦的公主,这会子只怕骨头都给敲散了!还容她躺在床上拿腔作势?”
就像,唐天霄对着任何一个宫妃都是那样温和多情,其实只是当个长长久久的太平皇帝而已,并不是真的对每个宫妃那样情深款款。
她说道:“我由她处置,只因你让我由她处置。这天底下再无一人可以决定我的生死,除了我自己,和……你。”
说完,他向守卫的内侍扬了扬手,这才飞快跑往正殿去了。
极平凡的梳子,半圆梳脊刻着流云的花纹,不过寥寥数笔,倒也简洁流畅,细看竟有些悠然出尘的味道。
当今宣太后久掌朝政,唐天霄又是至孝之人,因此此宫气势恢宏磅礴,并不下于唐天霄所居的乾元殿。
“如果不是她,也不是我呢?难道也必须让我们认下?”
可浅媚哽咽着冷笑:“嗯,宁淑妃用过的东西,我自是不配用。”
她趴到床榻上,皱着眉,笑得发苦,却又很快舒展开来,颊间一对梨窝深深,笑容随着眼眸的通透也那般通透明亮起来。
“打开看看。”
可浅媚冷笑道:“不告诉我,我便不知道么?还不是和我一样,被皇后栽污了,说我们谋害龙嗣?真真好笑得很,若她想嫁祸给我,早该避了嫌总不去我房中才是,还会帮我收拾东西,连个有毒的血燕也经了她手引人疑心?”
他犹豫片刻,又道:“这两晚他独寝在怡清宫了。可我不觉得他是在想那位故去了的宁淑妃。”
仗着一副好身手,仗着在北赫的特殊地位,她向来行事泼辣随性,刀里血里经历得不少,自以为聪明机警胆色过人,可如今,她才发现原来自己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坚强刚毅有定力。
第二日第三日,嬷嬷照旧过来问问她可曾想起什么可疑的人或事,见她一脸的迷糊,倒也不急着逼问,随即便离了她的屋子,继续去催问杜贤妃。
即便跑来看可浅媚这个被软禁的妃子,看守的内侍也不敢阻拦,竟由着他们一内一外,隔着窗子说起话来。
可他们,竟不约而同地保持了缄默,视若无睹,听若未闻。
太后身边的人,自然不会把区区一根金簪子放在眼里。
可为或不可为很复杂,喜欢或不喜欢却很简单。
沈夫人闻得她说女儿的不是,忙道:“淑妃这是什么话?皇后素来贞良贤德,你几时听说过她处事不公了?不过问几句话,便被你目无王法打成那样,还敢颠倒黑白,说她想活活打死你?太后娘娘,你看她小小年纪便如此血口喷人,是不是这番邦蛮夷之人,都没法说道理呢!”
唐天霄白了她一眼,“怕了?”
可浅媚叹道:“可惜我实在想不起那次到底送了什么,礼品里真的有血燕吗?当时托在宫女手里的,就四个锦匣而已。嬷嬷不妨找个懂北赫话的人去问问我那两个侍女,或许她们曾帮收拾过,多少记得一点。”
可浅媚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一点眉目:“我和杜贤妃带了礼物一起去探望贵妃统共才两次,第一次时我刚入宫不久,尚未得皇上如召幸。如果那时送了血燕,沈皇后这么个聪明人,想来不至于笨到陷害我没得宠幸就想着夺宠吧?那么必定是第二次了。第二次去时荼蘼将开未开,已经有点花香透出来了。嬷嬷去查一查,明漪宫里的荼蘼是什么时候开花的,便是我送血燕的日子了。”
唐天祺垂着头,忽然叹道:“若我父亲在,或者……或者我大哥在,断不容沈度猖狂至此。需知当年天下初定,满朝文武,十之七八是我那父兄的人,或者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皇上别无选择,只能选择重用外戚,并借外戚之力平制衡边关宇文氏、庄氏和图书之力……”
唐天霄很担心,但可浅媚真的记住了。
“我不过给你看一眼而已,什么时候说给你?”
可浅媚不屑地白了他一眼,道:“你以为我是养在深闺里的千金小姐吗?”
他也已注意到可浅媚远没有一般的北赫女子那般高大,甚至比许多江南女子还要娇小些。
可惜,她的夫,她的天,把她的命,看得比一匹爱马,一条忠犬差不多。
她远眺着南方一望无际的草原,叹息:“我也想看看,中原的景色是什么模样。”
他吐吐舌,做了个鬼脸,“不过多半会把你扔哪个冷宫里呆两天,到时我再去瞧你。”
她转头望向脸上爬满皱纹的嬷嬷,笑道:“嬷嬷说我是不是很聪明?连这个都能想得起来!”
唐天祺皱了皱眉,漫不经心地投往德寿宫正殿檐下的金龙和玺彩画,懒散道:“人人都说,杜贤妃嫌疑最大。”
再则,哪个心怀鬼胎的罪人敢要东要西,甚至记挂着打发时间的零食?
唐天霄气恼,“闯了一堆的祸还敢和朕置气!你胆子也太大了!”
其实沈皇后骄狂,宫中无人不知。
他反手搭上她柔软的腰肢,微笑道:“浅媚,你想让我猜是谁?”
“前儿御厨房里做了一味八宝小丸子,很是好吃,让他们再帮我做一碗来。再则日长无聊,请帮我装点水果或果子过来吃吧,桃子、李子和瓜子松子核桃之类的,我都爱吃。”
沈夫人应和道:“对呀,皇后也正为龙嗣之事日夜不安,急着要查出真相,哪里是有心要为难谁呢!”
可浅媚声音又有点沙哑,仿佛还在哽咽,眼睛亮晶晶的尽是水气,却弯弯地向上扬了开去,“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同心结。”
唐天祺暧昧地笑了笑,“又和我装!如果你真的看不出皇上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才特别开心,那他素日的心思,也算是白用了!”
“我惨了,我好像真的喜欢你了……很喜欢,很喜欢……”
她随口和内侍说的话,原来竟一字不落地传到了唐天祺耳中。
宣太后虽已年近五旬,依旧雍容贵气,五官秀丽,且有着和唐天霄一般的好看凤眸。
——盼他对着她时,眼睛里只有一个她。
可浅媚点头,“我不会弄丢……大约你才会弄丢吧?你那么多的妃嫔,给多少人留过梳子,打过结子?”
唐天霄忙伸手去抢,“喂,那是我的。”
嬷嬷望着她,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淑妃……的确聪明。”
宣太后道:“事关龙嗣,那是何等大事?怎容慢慢清查?何况还累皇后受了这等委屈,若不查出个青红皂白,如何对得起她?罢了,皇后现病着,少不得我这把老骨头活动活动,亲自来查上一查了。”
拿指尖拈住,轻轻一拉,竟是一枚同心结。
可浅媚失声道:“贤妃姐姐?她怎么了?”
她欣喜道:“唐二哥,你怎么来了?”
同心结发,结发同心。
可浅媚便红了眼圈,模样很是委屈,却到底立起身,随了前来引路的宫女出了大殿,一径往后面去了。
可浅媚疑惑地解开荷包,已见着一颗眼熟的玛瑙珠钻了出来。
她一眼能认出玛瑙丝带是她那日起床后丢了的那一条,而头发呢?
可浅媚眸子闪亮,笑容得意顽皮,却不答话。
她这样说着,显然也是不信这么迷糊的一个小宫妃有那等本领,能带着两个语言不通的侍女弄来那些宫中禁物来暗害他人了。
素常在宫中行走,他只穿着家常的杏黄袍子。
唐天霄笑道:“母后说得是,她出身北赫,马背上生活惯了,自是不像南方大家闺秀那般娴静。至于这个儿么……”
可浅媚甚至有点疑心,这嬷嬷暗中是不是受了谁的嘱托,一定要找出替罪羊来,只是万不能拉了她作替罪羊。
她眉眼如画,声音清澈如水,那样轻轻地叹息:“浅媚,你不该去。那个地方,那个人,有一点血性的女子,都不该去。”
嬷嬷踌躇了片刻,无奈地叹道:“问过了。淑妃娘娘的两名侍女,根本不认得血燕。这事儿……哎,且再查着吧,淑妃娘娘也多想想,平素还有哪些人可以进娘娘卧室,保不住有人心怀叵测暗地里来了个偷梁换柱嫁祸江东也未可知。”
嬷嬷叹道:“淑妃当真不记得皇上是哪一天赐的血燕了?也不记得是哪一天送给宇文贵妃的了?”
“五年了!”
“嗯,你纵她纵得也太过头,不然也不致这般无法无天。”
“哦,我来了!”
唐天祺倒也没打算隐藏自己的想法,倚着窗棂叹气:“我认为她比较倒霉,怎么就和你住在一起呢?”
周帝年纪渐长,行事甚有分寸,沈皇后虽然脾气大了点,尚能维持后宫祥和,于是她颐养天年之余,只在朝政大事上留心,并不过问后宫之事,竟不晓得可浅媚的样貌。
自然,也会传到唐天霄或宣太后耳中。
唐天霄又道:“我的妃嫔自然不少。摄政王还在时便为了娶了一堆的后妃,哪一个背后没有盘根错结的利害关系?又敢向谁真的倾心相待?我自己曾经中意的两个,你也早就知晓。雅意、清妩,如今各有所爱,朕枉为天子,却再不能挽回她们的心意。”
可浅媚醒来时已是清晨,而床畔已经空了。
唐天霄身体一僵,猛地拍开她的手,转过身愠怒道:“老是和朕提她,有意思么?”
唐天祺双臂趴到窗棂上,嘿嘿一笑,“没错,所以我只能在宫里四处走走,顺路看看你了。”
她说着,已小心把同心结放回荷包里,低头扣到自己腰间。
唐天祺叹一声,随手甩掉摘尽花瓣的残枝,答道:“那些事自有皇上料理妥当,你又何必想太多?便是真的拿她顶了罪,牺牲的也是他自己的妻妾,于你还少了个眼中钉呢!”
唐天祺笑道:“到德寿宫,自给太后请安来了。”
等可浅媚披着长发,背过脸去擦眼睛时,他已走过去,坐到她身边静默了片刻,取过妆台上的银梳放到镜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