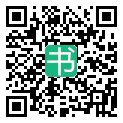第一章 夏日再见
声音温润低沉,非常动听。
此时,我身边这位顶级巨星现在正一只手支着下颚,徐徐道:“昨晚那幕戏要改,剧本我大概修了修。”
在我不负责任胡思乱想的片刻,他已经自行坐到茶几旁的第三把木椅上,把手里的文件夹放到餐盘旁,叠起了双手。
我忽然想起某本电影杂志上的影评——如果一个人长了顾持钧这幅容貌,除了当明星就没有别的出路了。他拿着一个文件夹朝我们走过来,且边走边和我母亲点了个头算是招呼,视线扫到我身上,一停。
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离座而起,可见还是应允了。
“是的,已经满了。我的生日在二月。”
看来她改变主意了,我大喜过望,一叠声的道谢:“妈妈,钱我会还给您的。”
“我叫纪小蕊,是梁导的助理,跟着梁导也有快六年了,”她把我安置在落地窗旁的小茶几上,她说话速度很快,从那给我倒咖啡的动作看,做事极为干练娴熟。她抬头对我一笑,马尾在她后颈里轻轻扫过,“我们虽然通过两次电话了,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本人呢,你看上去比照片里的还像梁导,都非常漂亮。”
在我贫乏的想象力中,剧本应该就是是一叠装订好的打印纸,我面前的剧本比我想象的漂亮多了。封面做得漂亮艺术,上写了四个极艺术的大字“约法三章”——我想起,这是电影的片名,其下是导演的名字梁婉汀和一个时间——那是开机时间。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很想翻开剧本看看剧透,但终于忍住了。
这个答案真够我尴尬的。我在她心中也就是这么个“没必要”的存在,甚至连提都不必提及。虽然她在我心中可能也差不多,但我毕竟有求于她,现在低声下气总是没错的。
十一年时间过去,顾持钧早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他极勤奋,一年至少有一两部电影问世;他几乎不演烂片,接拍的戏都是选了又选,极有口碑那种。他的演技也得到了认可,各种影帝拿了无数,算是现在国内身价最高的几个男影星之一,而现在的他正是我母亲这部《约法三章》的主角。
她刚刚站起来,那扇虚掩的门就被人从里推开了。
她以那种发号施令的眼神看着我,“不要这笔钱,你就别再叫我妈了。”
而秋季开学迫在眉睫。
“噢,没关系,”我说得很诚心。
有些紧张。
家里的积蓄很少,我动用了爸爸留给我的教育基金,爸爸的生前的朋友也慷慨帮助,一直撑下去,顽强地等着合适的器官捐赠者;好容易等到了合适的器官,他却终于没能熬过移植手术。
她的卧室很大,看上去和外面的客厅差不多大小,也有着同样壮观的落地窗帘,不过是全拉上的,看上去私密得多;酒店的房间大同小异,但总有个等级,母亲这间套间明显属于较高档次的。我也来不及细看,毕竟此时不说更待何时,“妈妈,我想跟你借点钱。”
当然,人是会变化的,我现在比三年前有用多了,绝对不会出现他看我一眼我就要紧张得死掉的激动心情了;但不幸的是,他现在距我不超过五十厘米,他衬衣领口的第一颗扣子没有扣上,我几乎能看清他劲瘦的上半身和起伏流畅的锁骨。
是的,面前这个气势凌人、美丽而高贵的的女人,是我的母亲。
她拿起酒店内线电话拨了出去,十秒钟后她放下了电话,盯着我说:“梁导叫你上去。”
“呀,你就是许真?请进。”
等等,他居然在看我?我后知后觉地发现。
“正尧,”她停了一下,“你爸爸的葬礼是什么时候?”
这笔钱真是烫手的山芋,拿,或者不拿,都是个问题。
不过,在电影界,男演员长得太英俊本身常会使人得出一个判断:无能。但顾持钧打破了这种陈规。在我母亲的电影《半生》中,顾持钧展现了日臻完善的演技。他在片中演十分逆反的儿子,和几位老前辈级的演员对戏,完全不输任何人。
现在这个时侯,说不紧张是假的。若干次试图提起了脚,又放下。我的行为实在愚蠢透顶,搞得酒店大厅的服务生频频对我侧眼相看,走过来笑容可掬地问我是否需要什么帮助。
我爸的主治医生傅寅医生安慰我说:他年事已高,熬不过是正常的。
“梁导演?”前台女孩抬起头打量我一样,虽然她克制的极好,但我依然看出她和善视线下的浓浓好奇和探究。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她在琢磨我和这位大导演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你的名字呢。”
我爸只懂得古生物,但我还是以他为傲,所以,有没有母亲对我来说,似乎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是我,”我犹豫了一下,轻轻叫出来,“妈妈。”
原以为是服务生去而复返,我随意往门和_图_书口扫了一眼,当即一怔,伸手去拿面包片的手僵在空中,还有点颤抖。
母亲拿起牛奶抿了一口,问他:“吃过早饭了没有,一起吃吧。”
意外变故就是这样,当它们汹汹袭来的时候,肉体凡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偶尔会对上他的目光,总能感受到他微笑眼神中的善意。
这并不是说没人能帮我,只是爸爸的朋友已经帮了我太多,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次求助了;找同学或老师,我完全相信他们会乐意相助——毕竟一直以来我人缘都相当不错。只是,我的窘迫境地必然引来一大堆同情的目光。爸爸生病的时候我已经看够了他们的同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实在不想采用这下下之策。
“小蕊,送她回去。”
“好,我看看。”母亲伸手去拿文件夹,“改到现在?”
“你姓许,许真,”他轻轻念了一遍,“不错的名字。”
站在2208号房门,我今天头一次镇定下来。
我跟父亲一起长大的,他是个古生物学家,涵养很好,我一辈子也没见过他发脾气;他的学识也很渊博,这在他的几大本著作里得到完美的体现。他发现了数百种从无记载的新物种;他能从一块化石中看出其中疑似网状结构的生物是生活在白垩纪或者第三纪,是木兰或者桦树;还能说出这种生物的习性和食物;他狂热的爱着自己从事的事业,长时间跋涉在外进行古生物考察,他的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浸泡着辛勤的汗水。
“呃?”
“谢谢。”我脑袋发热地感谢他,也不知道感谢的到底是什么。
“在学校吃过了,”我立刻说。
一样话说过三次、五次后,我也就不再多问了,不是我自吹,我向来都有着绝佳的领悟力。
大约是我所有的犹豫不决在来酒店的路上已经全部消耗殆尽,现在只剩下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勇气了。小腿不哆嗦了,急促的心跳变得平稳,出汗的手心也重新恢复了干爽,我稳着手心敲了敲沉重的木门。
“站住。”下一秒,她冷冷叫住我,听上去绝不愉快。
忍不住想起之前看过的我母亲拍过的一部电影《无休无止》,海报印刷得极其精美,画中的顾持钧和一位美丽的年轻女人对坐在路边的咖啡厅里,顾持钧抚着女主角的脸颊,额头相抵情意绵绵地谈情说爱,画面真是唯美得让人想哭;我也就是因为这张海报,脑子一热冲进电影院买了票,才知道海报上的画面只是一个幌子,开场五分钟后海报上的场景出现,顾维钧跪下求婚,在他求婚的一刹那,不知道哪里的子弹忽然而至,一枪夺走了年轻女人的生命。然后顾持钧开始了复仇之旅,一波三折的剧情,把他的演技展现得淋漓尽致。片中他跪在女友墓前失声痛哭的那一幕,现在还反复被人提及。这部电影让他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影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爸爸生病后我跟学校请了假回家照顾他,连续大半年没上学,只在最后考试的时候去了一下,成绩很不怎么样,又缺课太多,奖学金也在意料之内的失去了。
我已经是个成年人啦,虽然我很想把这句话振聋发聩地叫出来,但还是忍住了。她借给我钱,自然有权利知道我在干什么,更何况大四的课程不太紧,我点了点头。
我只是没想到她会露出这种被人戳到痛处的反应。
他轻轻握住我的手,那双手干燥清爽,指节修长,温热有力,我严肃考虑着几天不洗手。
只一眼,我的世界好像都亮了起来。
她愉快地笑起来,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叫我小蕊就可以了。”
于是我再次看了一眼他。这次确认了,他的的确确正在用那双漂亮的凤眼看着我。
我没法控制自己不看他。
母亲动作优雅地往面包上涂果酱,小口小口喝着牛奶;我也准备照做,忽然听到门又响了一下。我心里琢磨着着这门今天真是被开了关了太多次,如果门有感情的话,想必会觉得不耐烦吧。
于是我又大了胆子,再看了他一眼,这一眼比我想象还要持久且颇有成效,他的面容五官闯入我的眼睑——和我在无数照片电影里看到的一样:额头饱满,眉目疏朗,眼眸沉静,一眼望不到尽头。
我的确认为这事没什么关系,也不会迁怒我母亲。反正这么多年我们父女俩过得很好,我爸对化石和标本的兴趣已经盖过了一切,也从来也没有流露过没老婆的遗憾和失望。所以我想,我爸不会在乎她是否来观摩他的葬礼。
纪小蕊推了我一下,打断了我本来要发表的激|情洋溢的演说:“小真你收着吧,梁导给你了,你就拿着。她是你妈妈,又不是什么外人。”语气里大有劝诫之意。
客厅里很安静,豪华和-图-书的家具们都不动声色地彰显着酒店的品味和档次。我乖乖坐好,低下头去,茶几上除了一套咖啡杯,还有一本书。
我有点不好意思,“纪小姐,过奖了。”
“这几天拍电影到凌晨五点,梁导六点多才睡下,”纪小蕊说,“她刚醒没一会,还正在洗漱。”
“不用叫了,我就吃这份就可以,谢谢你,许真。”顾持钧拖过了我的餐盘,礼貌和涵养无可挑剔,缓解了我莫名的尴尬。我想,身为一个顶级巨星,顾维钧还真是如同传言那样,做人做得八面玲珑。
他又问我的名字,我毫无保留地说了。
他在跟我说话,这个事实让我血管都要不堪重荷了。不幸的是,他关于我身份的质疑足以把我的激动完全抵消。我有些轻微的尴尬,正打算说“不是演员”来澄清事实,我母亲已经抢先我一步开口。
我怀揣着那张滚烫的支票走出卧室,自觉脚步都蹒跚了。明明是一张薄薄的纸,却压得我腰都直不起来。我去沙发上拿我的书包,准备闪人。
因为我还太小。
于是我仔细地想了想,分析了又分析,在所有能帮我的人中,母亲经济实力最雄厚,我的学费对她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而她也最有可能帮我,因为我在电话里叫她“妈妈”的时候,她很清楚地答应了。
起初是做贼似的,鬼鬼祟祟瞥一眼,悄悄摸摸收回视线。我眼角余光中的顾持钧挺拔修长,穿得很随意,烫得笔直的衬衣和深蓝色的长裤,头发整整齐齐,至于五官,我太紧张以至于视线模糊,只依稀觉得,他整个人看上去好像都在发光。
这是个很有生命力的名字,就像这个名字的主人一样,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只能用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来形容,虽然带给每个人的雷声程度各有分别。
我正在心里“噼里啪啦”打着我的小算盘,母亲把签字笔放下,纪小蕊在旁边收好了支票本,“现在开始,每周来见我一次。”
她毫不留情地把话说到这么严峻的地步,让我愕然。我在心里默默咀嚼“妈妈”这两个字,安静地把支票收好。
母亲并不意外地扫我一眼,“什么事情?说吧。”
“二十二层,2208号房。”
“我约了人见面,我想知道她现在在不在。”
但凡有人听到“借钱”两个字都会露出这种“果然不是好事”的表情,我早就习惯了。不过既然对象是她,也许还有说服的可能。
我抿了抿唇,“梁婉汀女士。”
其实我也不想跟她借钱的,也不乐意诉苦,但确实走到了困境。
“早饭吃过没有?”
爸爸的葬礼之后,我最后整理清算了一下家中的财产,毫不意外地发现,我现在连学费和生活费的支付都成了问题。
去年这个时候,爸爸检查出得了肝癌,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我爸虽然在古生物学上建树颇多,但这并不能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我爸爸和大多数自然科学学者一样,完全不善理财,有钱就花掉或者用于购买新的研究辅助工具。
门“吱嘎”一声打开了,一道光流泻到走廊上厚厚的地毯上,我抬头朝门内看去,一个素未谋面的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女人正在对我报以十分亲切的微笑。
例如我面前这位的女孩,“梁婉汀”三个字让她肃然起敬,连念都念得字正腔圆。
我平生第一次叫出这个司空见惯的名词,那一瞬间,心情复杂得难以言喻。
“噢,没事的。”
“一起吃,”虽然我表示我已经吃过了,她对我的话置若罔闻,叫纪小蕊:“叫客房服务,两个人的早餐。”
我的嘴巴可以塞下一个鸡蛋了,又觉得不雅,迅速闭上:“您别这样,我很为难。”
这部电影当年骗了无数年轻人的眼泪,顾持钧也由此大红大紫,从此走上了光辉灿烂的明星之路。
“许真?”她连名带姓地叫我,声音听不出什么感情,干练而又冷静。
他的样貌非常好,那时候又特别年轻,这让他在起初的几年里,很演了一些感人时髦的爱情电影,跟女主角谈情说爱,无不哀怨缠绵。这些电影未必是跟我母亲合作的,但他积累了大量的名气。
这么大一笔钱,简直可以砸晕我了。
母亲看了我一眼,勺子搅着咖啡,“说说你吧。”
语气很平和,一听就是熟悉了若干年的老朋友语气。这也难怪了。据我看到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娱乐新闻,总结出来两人的大致经历如下:顾持钧在二十岁左右遇到了我母亲,我母亲那时已经是个颇有名气的导演,她很赏识这个年轻人,让他在自己的电影里担任了一个小小的配角,这部电影合作下来,他从配角升为主角,接演了一部爱情电影,故事里的男女主角是对笔友,相隔千里之外,每天坚持通信;有一天女孩不再
和*图*书来信,男孩循着信封上的地址找过去,才知道她已经因为绝症去世。
我垂下视线想了想,俯下身重新写了张欠条双手递过去。我跟她相认只因为她是我妈妈,并不是为了要她的钱。她这样强行让我背负巨额债务的行为真是让我又无奈又悲催,按照现在的银行利息算,一年下来,我竟然要还她几千上万。真是太可怕了。
前台的年轻女孩笑容可掬,“请问是哪个房间的客人?”
纪小蕊看到我的目光,很善解人意地开口,“我去看看梁导。”
等到两人吃完了饭,看着我母亲伸手去拿顾持钧带来的飞单,心知他们又要陷入一场关于剧本的讨论里去,我立刻插了话。
不用她说我也感觉到我母亲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往好了说是果断坚定,往坏了说就是武断。偌大一个影视圈里最有名的女导演,没点慑人的本领怎么能在这个圈子里站稳脚跟,她绝对不喜欢有人违逆她的意思,不论那个人是我还是别人。
在别人的地盘,总归要谨慎点。
我注意到她眼角一丝轻微的皱纹,眼圈下方有些发青,她明明化了淡妆但怎么都掩盖不下浓浓的倦意。一个多月前我在电视上看到她新电影的开机仪式;自那以后,关于这部电影的各种新闻就在报纸电影的娱乐栏目上频频出现,前期的宣传可见一斑;这部电影是这两年来投资最大的电影,几个主演也都是现在最当红的大明星,一举一动都会被写到八卦新闻里去,而她一个人要当好这么一部大片的导演,不受苦受累是不可能的。
母亲凝神想了一想,颔首说了句“也好”,就回到了餐桌旁,拿起顾持钧送来的几页修改的剧本看了起来;顾持钧却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修改的剧本上,他隔着宽敞的客厅朝我看过来,唇微张微合,无声地跟我说话。
她坐到书桌前,我也占据了小半个桌角,从书包里往外掏纸笔写欠条。我学经济学,写欠条这种东西对我来说轻车熟路,我俩同时完工。我写下的数额是不多,可看到她给过来的支票才发现,她在支票上写下的金额是三十万。
母亲脸上的神色也充分说明了我的可笑,她摇摇头扫我一眼,“不要自作主张。小蕊,打电话。”
只是……时不时看顾持钧一眼。
保险负担了绝大部分医疗费,但爸爸沉疴病床近一年,总有一些花费是保险范围之外的。
“许真,”我说,“我的名字。”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也意义非常,就是这部电影后,我成了顾持钧的粉丝。
“你也应该是大学生了,”她垂下眼睑说了这句,又问,“你今年二十一?”
就像有人拿着一把钢钎往我的五脏六腑扎来,我眼睛鼻子同时发酸,喉头哽了一下,“三个星期前。”说出来才发现,声音还是有点哆嗦。
递到她手里的借据,她看都不看就扔进了碎纸机。
末了会干巴巴地对我说“你妈妈现在很忙,她空闲下来就会来看你的”。
他只演电影,对出唱片完全没兴趣。倒是有点浪费这把好嗓子。
那一瞬间,顾持钧的表情只能用异彩纷呈来形容,不胜惊讶、难以置信交替出现;不过不愧是影帝,下一秒就恢复了镇定,让我以为他的惊讶是我做梦的时候看到的。顾持钧和我母亲认识、相熟整整十余载也是头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我的存在;那么我敢打包票,母亲是个极为注重隐私的人、也是极为自我的人。
逼上梁山的借钱并不好受,总之,过段时间后一定要找个机会还掉这笔巨款。
“不是保密,”我母亲却说,“是没必要说。”
——“许真,再见。”
她再次打量了我,说:“我以后叫你小真吧。”
“小蕊,进来,”母亲吩咐她,“拿支票本和笔。”
她点了点头。她既然生了我,应该还记得我的生日。
“差不多,就睡了两个小时。也不急这一会,剧本你吃了饭再看吧。”顾持钧一手压住了文件夹,视线从我母亲身上转移到我的脸上,朝我露出一个那种只有成熟男人才具有、能让异性心跳快十倍的亲切微笑,“这位,是新演员?”
她盯着我,声音近乎严厉了,“正尧难道没留下钱给你?你居然连学费都拿不出来?”
抬起眼,通往卧室的门半虚掩着,我忍不住朝门内看了两眼,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有人从门里出来,让我措手不及。
“不论如何,还是谢谢您。那我告辞了。”
“借钱?”她皱着眉头,仿佛听不懂我的话,好像我说的是古埃及语或者西夏语。
“保密做得真好,”顾持钧咬了一口面包,跟我母亲说,“梁导,我居然一直不知道你有个女儿,而且都这么大了。”
母亲静了一瞬,仿佛想起什么,低头喝了口咖啡,才说:“那时我在国外拍外景,https://m.hetushu.com.com回不来。”
她边在电脑上查询边问看我,“客人的姓名是?”
坐吃山空。
她就用这种审视的视线扫我一眼,好像把我完全看透了一样;我脊背一麻,下意识弹跳起来,那悦耳而不失威严的声音传入耳中。
顾持钧。
“噢,小蕊姐,”我想了想,还是加了一个“姐”字。
我母亲抬头看他一眼,随口问:“持钧,什么事?”
“不是,”她就这样毫不避讳地解释我的身份,“我女儿。”
很小的时候也傻乎乎的问我爸“为什么别的小孩子都有妈妈而我没有”,因为每次提到这个问题,我爸都会放下手里的论文或者化石,端正的脸上出现一种神秘莫测的表情,似乎他被天大的问题难住了,黑框眼镜后的那双眼睛显得既困惑又愧疚。我也是长大之后才明白,我爸那不可言说神情的隐含意义——他的确想要告诉我一点什么,但每次话到嘴边又欲言又止。
有顾持钧在场的情况下,我觉得这话题难以启齿,低下声音:“能单独跟你谈吗?去卧室,可以吗?”
这种“被面试”的语气让我有轻微的不适感,我微微紧了紧眉头,还是和盘托出:“静海大学,大三,噢,我是说,秋季开学后就是大四了。我在商学院经济系就读,成绩还不错,之前是班上的学生代表,也是院里的宣传部长。”
纪小蕊冲着来人熟络的打了个招呼,又回头看着我母亲:“梁导,顾持钧先生找你。”
“是电影剧本,”纪小蕊解释,“你来之前我正在看。”
纪小蕊应了一声,我赶忙说,“不用了,我认识路的。”
我匆匆伸手跟他相握:“啊,顾先生,你也好。”
当真是明星中的明星,不论走到哪里都那么耀眼。
“钱哪里会有不需要?”她冷淡地扫了我一眼,“除了学费,你的衣服、裤子、鞋都该换了,品味太差。头发也应该打理一下,现在这样,实在难看。”
“妈妈,我有事想求你帮忙。”
我回了他一个笑容,再深呼吸一口气,摆了摆手示意自己一切都好,然后踩过明亮得可以照人的大理石地板穿过酒店大厅,走到前台,以一种毅然决然不跳黄河心不死的语气开了口。
关于我的母亲,我能说的其实很少,因为在我生命最初和现在的岁月里,我的生活里从来没有母亲的存在。
说话间,有人叩了叩门。
我走神了片刻,终于听到了从我母亲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这之前,我母亲都在等着喝咖啡,纪小蕊往咖啡杯里放了小半杯牛奶、三分之一块方糖后,她这才拿起了咖啡杯。
话已至此再没别的好说,只当这趟白来了。我转了个身,拉开卧室门打算离开。
纪小蕊坐在距门很近的沙发上,听到铃声,她放下掌上电脑去开了门。不出我所料,是客房服务,服务生把早餐整整齐齐在桌上放好。早餐很简单,双面烤的焦黄的面包片、颜色喜人的草莓酱,还有一壶牛奶,两个鸡蛋。
说不失望是假的,我竭力做着心理建设。说来也是,忽然冒出的女儿来借钱,谁都不乐意的,现在骗子这么多,没准她会认为我身份可疑呢。她的犹豫,完全在情理之中。
这让我更清楚的看清了她的容貌:就像无数八卦新闻里形容的那样,她的外表看上去更像是个一流的女演员而不是导演;她的真人比照片和视频里的更年轻,她今年应该是四十岁出头,可看上去绝不超过三十五岁;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极为有神,视线所到之处就像此时的阳光一样,让一切无所遁形。
“你爸爸不在了,我应当管教你。”
纪小蕊答应了一声就去打电话了,剩下我和我母亲在茶几旁独坐。我抓空心思的想着话题,和素未蒙面的母亲见面的尴尬就像过夜的水一样喝了个十足,茶几上的杯具们嘲弄地看着我,我大腿抖了抖,茶几微微震动了一下,咖啡泛起了一圈圈缓慢的涟漪。
这是我第一次在外人面前提起这个名字。本以为这三个字我会说得十分艰难;让我意外的是,那三个字忽然就有了力量,像跳跳糖一样从我嘴中蹦出来,诧异的同时,我的心情顿时微妙地放松了一大块。
我们的视线在空中撞上。顾持钧容貌俊美,眼神极其迷人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上一次我跟他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是在三四年前的事儿,那是在他代言的某产品见面会上——他当时在台上环顾四下,眼神在我身上略微停留,对我微微一笑,示意抽中签的我上台参与一个小活动;其实那个眼神和微笑不过是转瞬的事情,我可怜的心脏几乎不堪重荷,差点爆掉。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什么叫被电到?这就是!
他吃饭的姿态很优雅,修长的手撕着面包,微微低垂眼睑;就像他在电影里的一贯形象。和_图_书
我眼睛发直地盯着门,首先看到身穿黑色坠地长裙的女人从里面门内信步走出,修长手臂和脖颈的皮肤轻轻巧巧地裸|露出来,白皙的肤色和那身如水的黑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全身几乎没有任何装饰,除了脖子上挂着的那串银色的项链——项链垂到胸口,最下方悬着一个“L”形状的吊饰,反射着明亮的星光。
活生生的顾持钧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真的站住了,大惑不解地回头。她却不看我,叫客厅里的纪小蕊。
“我可真是没想到,”他摇了摇头,对我露出炫目的笑容,又在茶几上方伸出了手,认真同我招呼,“你好。”
“我不借很多钱,只要能支付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就可以了,”我怕她想多,连忙解释,“我已经大四,只差一年就毕业了,都到这个时候了,我也不打算跟学校申请减免学费……再说我还有同学比我更需要学校的奖学金。”
我不做声地摇了摇头。别说学费,我现在连两千块都没有。
但这些话题到底和我平时的世界相去甚远,我插不了话也不想去插话,干脆不做声的傻坐着,静等他们吃完饭。
照例上说这是个问句,虽然我没有听出来其中的询问感。
她不答,脸色阴晴不定地看着我。
这个人是受过训练的专门演员,随便的视线都带着可怕的杀伤力,英俊得让人不敢直视。我需要在桌下攥紧我的手,费极大的力气才能控制住自己的心情,不让自己的花痴表现出来。
我十五岁前,爸爸每次出门都带上我,我们去过偏远的山区、浩瀚的沙漠、荒凉的海岛……我们在裸|露的地表寻找露头的化石;我见过那么多新奇别致的景色,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这对开阔我的心胸是有好处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进一步解释说,“生活费我可以自己挣,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兼职。我打算上研究生,我的导师钱教授说帮忙,我肯定能申请到奖学金。妈妈,这笔钱我会在两年内还给你的,我可以马上写借据。”我吸了口气,期盼地看着她,“您看怎么样?”
本着节约粮食的原则,我把自己面前的餐盘推了推,说:“这份早餐我还没动过,我来之前已经吃过饭了,顾先生你——”话到一半忽然哑住了,顾持钧是什么人,怎么会吃我不要的早饭。
我几乎被那光耀花了眼,一时间无法分清是那光是从吊坠上迸射出来还是来自于她那淡然沉稳的气度,实际上,我也无暇去顾及这样的小细节——因为,她正朝我走过来。
这时,素未蒙面的母亲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刚刚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讣告,向我表示了深切的慰问;我想,再怎么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而我也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她慰问一下我也在情理之中;慰问后又过了两天,也就是前几天,她再次跟我联系,说自己回到了静海市,跟我约定了见面日期。
他凭借那部电影,首次拿到了国际电影节影帝提名。
“没,”顾持钧摇了摇头,神色中露出一点迷茫的倦意,“醒了就过来了。”
实际上我昨晚想着今天的见面,根本没睡好,今天一大早就醒了,在空荡荡的寝室里呆了一会,又一路小跑去学校的餐厅,匆匆忙忙吃了一顿新鲜出锅的早餐。然后我就坐上地铁和公车,还经过了一座跨海大桥,在唾弃这个城市实在太大和无穷的煎熬中,花了足足两个小时零一刻,辗转到了这座坐落在城市南边且靠海的酒店。车船颠簸明显消耗了我的体力,我忽然觉得有点饿了。
两人缓慢吃着早餐,时不时聊上一句关于电影的话题。听他们的对话,我才知道他们现在能坐在这里吃一顿早饭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连续两周他们都是凌晨四五点钟才睡觉,今天是执行导演在拍几幕不那么重要的戏,他们才得以休息。
我一怔。我虽然穿着打扮都不是什么名牌,但也算清爽整洁,想不到在她眼里竟然这么不入流。鉴于她如此豪爽地给了我这笔钱,我暂时不打算跟她争论我衣服的品味问题,只是颇诚恳地建议:“就算是这样,这也太多了,再说——”
就像无数次我从电影里看到的他,虽然隔山隔水,却总能走到人心里去。我能读出他的意思。
我身处的地方是这栋豪华酒店的一间套房,色彩沉稳,格调典雅,就这座像酒店的整体风格;客厅很大,四五米宽的落地窗帘半遮半掩,漂亮壮观,可以远眺蔚蓝的天空、俯瞰城市的街景,还有远处蔚蓝色大海,一望无际的海平面延伸到。早上的九十点钟的阳光透过薄如蝉翼的玻璃,毫不吝啬地撒了满屋。
“哎,好。”
明明双脚已经站在了酒店门口,我却再一次踟蹰起来。
我傻了眼,“啊啊?我真的不需要这么多钱啊。我只借学费和住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