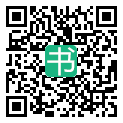第七章 爱要留到最美的地方说
2
浑身的血液都涌上来,无法遏制,他也不愿遏制——他不知如何形容那一刻的感觉,好像旅途上濒临枯竭的路人,在黄沙大漠中终于发现一处绿洲,飞奔过去却发现不过是镜花水月海市蜃楼。许明智还拉着他,涕泪横流,许隽曾给他看过父母的照片,依稀记得那是个尔雅温文的中年男人,意气风发;如今额上尽是沧桑刻下的纹路,十年铁窗生涯已磨掉他所有的骄傲。有那么一刹那他气得恨不得当胸口踹过去,却迈不开步子,千钧的重量都压在胸口,呼吸不得,喘息不能,只听到自己牙齿格格作响的声音。
“以后我们家的家事,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昨天晚上去医院拆了石膏。”
其实他想过反驳的,他想反驳说若不是你做错事在先,我姑妈纵有通天的本领,也摧不散你的家庭,这话在胸臆间徘徊涌动,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以前是我女儿不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妄图高攀凌家,我们已经知道错了,”他伸手拉着凌千帆的袖子,老泪纵横,“图书馆的这份临时工也不容易,早上闹钟到五点我就醒,生怕迟到几分钟。晚上我走得最晚,有没有人去借书我都不敢打马虎眼,现在就靠这吃口饭……”
他未加反应便拨过去电话,贝菲的声音听不出冷热:“我在上班,有什么事?”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其稀有,而且恰恰好到死为止,没有后续。
“请问许叔叔在吗?”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现代社会科技手段如此发达。陈嘉谟带着私家侦探,让他们做人像拼图,试图描画出这个外地男人的相貌,送回来的拼图却让凌千帆更为震惊。
“阿三,我们去新藏线。”
他拖人给许明智安排了份区图书馆的临时工,算到他下班的时间去许家的旧宅。九曲回肠的深巷里,十余年前还算是繁华地段,转眼间城市建设日新
和_图_书月异,一路走进来,外面已有不少地方,挂着“拆迁”的牌子,许家所在小区能得以存留,已算幸运。进来的路被外面的工地挤得只余羊肠小道,好在他已来过几回,循着记忆趁着月色进来,顺利地找到许家所在的单元。大门上绿漆斑驳脱落,生锈的铁牌上门牌铃已有些歪斜,很使劲地摁下去才起了效果,微弱的红光闪烁,响了许多声后才传来沙哑的声音:“谁呀?”
凌千帆十指骨节已攥得泛出微白,怎有心情理会他这等笑话:“那许明智对贝菲呢?是冷淡还是……讨厌,或者……”
他在街上发疯般的奔跑,海风的咸腥味混杂在空气中侵入口鼻,浑然不知自己跑了多久。他脱下鞋子,发狂地扔向远远的海面,海水在月下闪烁着妖蓝的颜色,细细的沙砾挤进脚趾缝,远处有灯塔海港、微涛拍岸,宁谧的夜里只余海水轻拍沙滩的声音。他一口气冲到海里,一个浪头过来,海水呛到口里,腥咸涩口的味道,让他剧烈咳嗽起来。他软倒在浅滩里,海水不断地冲击着他的身体,冰凉蚀骨,而他只是静静地躺着,任海水冲刷他已麻木的身体,已麻木的心。
凌千帆反手轻敲着办公桌,发出清脆的笃笃声,陈嘉谟忽又想到什么,笑道:“贝菲可有趣了,我看她平时总叽叽喳喳的,那几天格外安静,问她是不是怕说多错多,结果贝菲鼻孔朝天哼了一声,说:我生平最恨出轨的男人,见一个阉一个,见两个杀一双!”
凌千帆拉好铁门,许明智指指凳子,找了半天才摸出个杯子,在厨房冲了冲,倒水出来端给他,战战兢兢的。
情感告诉他他应该立刻赌咒发誓不会再有此类事件发生,理智却告诉他也许……也许还会有下一次,姑妈对贝菲成见已深,且不论贝菲遭险究竟因何而起,她对贝菲的态度已很难转圜。他踱至窗边,推开一丝缝隙,三月间的春和*图*书风还透着丝丝寒意,轻飘飘地打在他额上,让他有些微清醒过来。
“然后再等着下一次同类事件的发生?”
他声音如此微弱,却又如此坚定,挂上电话后他从床上蹦跶起来,窗外艳阳高照,雨后天晴,格外灿烂。他霎时涌出豪情万丈,摸出手机啪啪地 摸出手机啪啪地按下去:“给我准备一辆重型途锐,加装越野备胎,我回来就去试车。”
他闭着眼不愿看清眼前这一切,艰涩地想反驳她,却不知如何说出口,只能再倔强一回:“阿三,再给我一次机会。”
飞机在婺城上空缓缓减速,横亘婺城的江上灯火璀璨,如缀在夜幕上的黄金锦带。贝菲不知道他今天的飞机,接他的是陈嘉谟,一脸的狐疑,想问又不敢问,凌千帆扯扯领带笑道:“取一笔现金,送到许明智那里。”
“鄙姓凌,草名千帆,贝菲的男朋友。”
湿湿的海风捎带过咸咸的味道,黏在人脸上,北方的春天来得晚,漫山的杜鹃尚未盛放,连天也迷迷蒙蒙,未见仲夏时的湛蓝。他难以形容此刻的心情,说复杂倒未见得,毕竟吐了一口气,却怎么也谈不上欢畅。
陈嘉谟愕然,凌千帆挥挥手道:“我看有必要亲自去一趟大连。”
“我真的相信你,”贝菲别过头来,不哭不闹也不冷嘲热讽,“你对我很好,从小到大,再没人对我这么好过。”她伸出右手来,凭记忆掰着指头数那张全家福上的人,“爷爷,姑妈,妹妹,表弟,我顶多也就排第五吧。”
他确曾怀疑过姑妈,贝菲一出事时他便想到了姑妈头上,后来山重水复,竟发现贝菲原来是许隽的旧识——有那么一瞬间他是怀疑过贝菲的,为她瞒他瞒得这样深。不过这念头现在想来也觉得可笑,谁会拿和-图-书自己的性命去开这样的玩笑?况且许隽和贝菲再亲,也是十年前的旧友,贝菲这样精明的人,何至于拿现在的幸福去冒险。
“阿三,”喉咙痒痒的,他咳了咳,声音干涩喑哑,“你胳膊好了点没?”
呲呲哑哑过后是话筒掉落下来砸在墙上的声音,嘀的一声,大门开了。
陈嘉谟犹豫良久才颇不肯定道:“说不好,他好像想和贝菲说话,又好像不太敢,老实说我很奇怪,总觉得他们以前好像认识。不然……这许明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找贝菲的麻烦,但是这……我实在想不出来原因。”
“他们以前确实认识。”
连环追命电话叫来了陈嘉谟,让他细细回想一路上的事,不可放过半点细节,陈嘉谟蹙眉道:“我们搭飞机回去的,路上贝菲和许先生都在休息,我想贝菲可能心情不好,不大愿意和许先生说话。后来……贝菲说她要单独和许先生交代事情,我就去联系公墓,请人看风水,买了块墓地。下葬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去了,贝菲在路上买了花篮,好像……也没有什么异常的。”
他转过身来定定地瞧着贝菲,决绝地说:“再有下一次,我凌千帆就真他妈不是个男人!”
拖把停留在他面前时许明智抬起头来,还是那张昨天恍惚中不断在脑海中闪现的脸,皴裂粗糙,战战兢兢。他知道许明智昨天说的话并没错,“我已经坐了十年牢,好死不如赖活……”
拼图出来的人,居然和许明智如此相像。
他恍惚间明白,姑妈警告的对象不是贝菲,而是他自己——你纵然给贝菲金钟罩铁布衫,我一样能让她知难而退。
电梯老旧,他换走楼梯,灰暗狭窄,仿佛一不小心便会沾上灰尘。他极小心地上了三楼,房子是新装修过的,外面的铁门上换了新的绿纱,新上的木门洞开,电灯惨白幽暗,许明智苍老的脸上布满皱纹,双目深陷,颤巍巍地拉开铁门的闩:“请
hetushu.com.com进,请问……你有什么事?”然后他去了趟许明智工作的区图书馆,大理石地板光鉴照人,没什么人来借书,许明智正拄着拖把认真地拖地,拖几步就趴下来看还有没有污迹——大约是眼睛不好的缘故。
总算和姑妈无关,他第一反应竟是松了口气,其实现今的社会,谁有那么轻易说能脱离家庭?曾有一年他去新德里和印度政府谈笔大单,才知印度青年男女多靠相亲来完成人生大事,无他,只因种族宗教必须一致,仅此一条便大大缩减配偶范围。若不服从家族安排,则是和整个家族乃至于整个教派、种族的对立,没有什么人真能斩钉截铁地说,能背弃血脉相连的父母、抚育自己的家族。
一时的义气是最容易不过的事,难的是随后孤清寂寞的漫长时光。
回到酒店时浑身湿漉漉的,酒店经理差点没认出他来,进房时镜子映出他狼狈不堪的模样,发丝乱糟糟地搭在额前,西服湿透,脸在灯光下显出几分青色,他自己看了都不免惊骇。拿起花洒任热水冲刷身上的盐渍,等他整个人清明过来,窗外已泛鱼白,他拉开被褥缩进去,迷迷糊糊中听到手机响,摸出来一看是贝菲的短信:天气预报说今天北京沙尘暴,自己小心。
嘱咐陈嘉谟留下帮他坐镇婺城,跟贝菲说北京那边有重要的招标会,要他亲自出马。
庆幸活在并不那么顽固的时代,虽然他的自由需要更多坚持,现在的结果再好不过,宽心之余却又不免疑惑,许明智何至于要对贝菲下手?因为许明智的外遇,贝菲似乎对他存有芥蒂——猛然间他忆起汪筱君过世后,陈嘉谟和贝菲送许明智回大连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许明智和贝菲之间,明明是知道彼此的,为何竟由始至终,表现得毫无交集?
橱架上搁着民国年间仿明宣德青花瓷瓶,那还是他从琉璃厂淘来的,他拎起瓶口朝窗棂上砸过去,噼噼啪啪地声音
和图书清亮悦耳,落下满地青白的碎瓷,溅到脚边数片,许明智像只惊弓之鸟,扒着沙发扶手,瑟缩不已。这一次他没再称呼许明智为“许叔叔”,他只希望和那段痛苦回忆做一个了结。
他酝酿着如何开口,实际上一路上他设想过许多次,或许他该进门便给许明智一个下马威,或许他该委婉动人曲折入手……他还没想好究竟何种策略最为有效,许明智脸色煞白,瘫倒在木沙发上:“凌……你也是凌家的……”他畏缩着身子,颤抖地攥着茶几,求恳地望着凌千帆:“凌少爷,我已经死了老婆孩子,现在只求安安稳稳地活两年,不知道什么时候眼睛一闭两腿一伸,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求你们高抬贵手,别让我这个半截入土的老头子夹在中间难做人……”
他的话掷地有声,教贝菲也吃了一惊,看他倚在窗边,挺拔峻秀。原来就觉着他像古时候的泼墨山水,淡浓得宜,灵秀而不失气度,现在这感觉越发的深刻,不过以前那些线条都是柔和清淡的,现在却难得的入木三分起来。她心底夹七夹八的情绪交错混乱,说不清是欢欣还是伤感,如隙缝里飘进来的微风,明明捎着春寒,却夹杂着点滴温润的气息。
陈嘉谟比了个咔嚓的姿势笑道:“凌少你可要小心啊,什么时候被贝菲误会可就麻烦了。”
两人进入冷战期,他载着贝菲回心湖苑,她却整日里拧着不搭理他。凌千帆琢磨甚久,觉得根源还得着落在考察队在怒江被围殴的事情上,两边都抵死抗争,谁也不像是在说假话。当初为免事态扩大,当地公安局也只是把参与围殴情节严重的人员拘留了一段时间,陈嘉谟按照他的吩咐暗中调查,最后煽风点火的主使承认是受人指使,根据描绘大约是五六十岁的外地男人。但是双方仅有一次会面,事成后报酬也是通过网上不记名帐号转手数次后汇过来的,看得出此人也颇为谨慎,倒让凌千帆颇为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