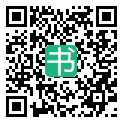上册
第二十八章
郭泉海对冯妙倒是十分客气:“婕妤娘娘大约没做过刺绣这样的活儿,只要把原来的线剪掉,用纯色的丝线重新绣一遍就行了,不用整件都重新缝制。今天开始日夜赶工,还是来得及的。”
他把礼服略略展开一点,把上面一处鸾鸟的尾羽指给太皇太后和高太妃看,果然在五色尾羽中间的赤红、湖蓝两处,夹杂着些颜色不纯的浅色丝线。他再次跪倒:“对陈留公主的礼服不上心,就是对太皇太后和皇上不敬。老奴自知失职,甘愿罚俸,向太妃娘娘请个旨意,让老奴把那个胆大包天的侍工,也一并处置了。”
拓跋宏拍开泥封,尝了一口,笑道:“很好的酒。”他把酒坛托起,递向冯妙,让她就在自己手边也喝了一口。大约是船身摇晃,这一口喝得急了些,冯妙捂着嘴咳嗽。人伏在船舷上,刚好看见水波里映出的圆月。
她平静地抬眼,迎上拓跋宏的目光:“《晋书》上说,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皇上总有一天,会建立名传千秋的功业,在那以前,自然要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满池波光明亮,她的眼睛却是千万波光中,最亮的两点星光。
“陪我出去走走,”拓跋宏推开一侧的雕花小窗,隔着殿墙向她伸出手来,“你敢不敢?”他嘴角含着笑,故意挑衅,他知道冯妙的内心,并不像她外表看起来那么柔弱。她不怕危险,也不怕未知的一切,她和他一样,无论前面有什么,总有一直走下去的勇气。
说着,她就理理衣角蹲下来,伸手去扒桂树下湿润的泥土。拓跋宏在她手上轻轻一拦,自己挽起袖子去挖。
郭泉海跪在地上不敢起身:“老奴的确尽心尽力地替太皇太后和太妃娘娘办事,连刺绣礼服的侍工,也选的是上次太妃娘娘赞不绝口的那一名。老奴不懂刺绣,见礼服精美,就呈上来了。可是刚刚才听说,负责刺绣的侍工予星,为了赶工,竟然敢偷懒,用杂色的丝线绣制。”
高太妃身边得脸的宫女绘秋,正把单子念给太皇太后听。纯金镶东珠冠顶,大红百鸟百子礼服,还有数不清的首饰、金银器皿、梳妆用具。太皇太后也不可能每一样都展开细看,听绘秋报了一遍名字,便对高太妃说:“辛苦你了,准备得很好。”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直白地对她说话,“你的眼睛,像一轮圆月分成的两片”,心口像装着一盏滚烫的热茶,躁动不安中氤氲升起袅袅令人沉醉的迷眩。
四面是水天一色的沉沉暮霭,波光无声荡漾。仰头便是灿烂星河,宫殿楼宇、朝堂后宫,一切都离他们远去了,只剩下渺茫之间的一叶扁舟,还有两个人、一壶酒。
原来又是郭泉海,他动不得冯妙,就要先在予星身上下手,三番两次寻她的错处。冯妙轻拍她的背:“幸好你做事认真,先把绣好的部分清洗干净,现在还能想办法弥补。不然,真等到这些绣品交出去,才被人发现,那才是大麻烦。”和图书
冯妙听了却觉得有些诧异:“怎么?宫里用的布都是采买而来的吗?”她虽没亲自做过,却知道冯家一直有自己的蚕娘,养蚕缫丝,再织成布匹。不光冯府如此,许多小门小户的人家,也会自己养蚕织布,不但能供应自家使用,还能拿出去换钱补贴家用。
冯妙不能在白天拿出来,只能等夜深时,才躲在内殿偷偷赶着做。丑时过半,冯妙实在太过困倦,忍不住伏在绣案上小睡了一会儿,却又被一阵咳嗽惊醒,手摸到几案上,喝了几口冷茶,才勉强压下去。
话才传回来不过两天,予星就匆匆忙忙地赶来了长安殿,向林琅见过礼后,就一脸焦急地对冯妙说:“婕妤娘娘,这次我恐怕是真的惹上麻烦了。”
等她出门时,冯妙也借故向林琅告辞,两人一起走出长安殿,冯妙才说:“虽然现在动不得郭泉海,也不能由着他继续妄为。上次我画给你的图样,夹在林姐姐给你的赏赐里直接带回去,居然也会被别人知晓,你身边一定有向外通风报信的人,我们也将计就计一次,把这人给揪出来。”
她继续埋下头,认真数着手里的线股,却听见雕花轩窗下,传来一声低低的叹息:“你这副神情专注的样子,真是……我从没见过我的生母,可我总觉得她应该就是这副样子。”
两名宫女举着丝缎嫁衣,在日光下一寸寸展开,看向嫁衣的宫女、太监都露出惊异神色,连太皇太后和高太妃,也一瞬不瞬地看着嫁衣上的吉祥图样,似是不敢相信。
冯妙盯着他的手掌看了片刻,他们是夫妻,却要这样跳墙出去相会,实在荒谬。可不知怎的,她宁愿像现在这样,也不愿再进崇光宫。她用纤细的脚钩起床榻边的珍珠丝履,人撑着雕花窗棂跳上去。拓跋宏在窗外张开双臂,让她稳稳地落在自己身前。
看清来人,冯妙立刻起身,隔着窗子就要跪拜下去:“嫔妾叩见……”话刚开头,却被他扬手打断:“今晚陪我说说话,别见那些虚礼。”
婚事一定,北魏皇室与丹杨王刘昶就成了姻亲。刘昶原本就是南朝宋文帝的第九子,讨伐南齐名正言顺。有了这个理由,拓跋宏很快就颁布了第二份诏令,“借兵”给丹杨王,讨伐南齐。说是借兵,刘昶不过担了一个虚名而已,这场战争的主力,完全是北魏的兵力。
拓跋宏轻笑一声:“隐忍……不知道要隐忍到何年何月……”他指着天上的月亮,用带着醉意的嗓音说:“你知不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轮圆月。自己梦寐以求却得不到的,总希望弥补在心底的月亮身上。瑶妹是公主,她不用学权谋算计,不用跟人明争暗斗,她只需要长大、嫁人、生子、白头。”
拓跋宏抬起头,迷离的醉眼看向拥抱着他的婕妤,圆月刚好在她身后,给她涂抹上一层清霜。身上被冰冷的夜风一吹,忽然变得滚烫起来。他俯身,衔住冯妙露在棉布外的一点指尖。和图书
月光铺满窗棂、绣案,如同一层水银一般。她借着月色细看刚才的针脚,忽然觉得窗外似乎有人影,她警觉地抬头,窗外却什么人都没有,仍旧是那两棵槐树和桂树相对飘摇。
“就这么放过郭泉海那个老东西,我不甘心!”予星在他手底下,没少吃苦头,这一次又差点被他害得赔上性命。
冯妙看她焦急,叫她先喝杯茶水,再慢慢讲。予星双手捧着茶盏,口中说得飞快:“我也知道给公主缝制嫁衣,事关重大,所以郭公公送来布料的时候,我特意带着人仔细查看,确认那布料质地是上好的,这才收了。”
“不能喝就别喝了。”拓跋宏掬起一捧清水,轻拍在她额头上。
“妙儿,”拓跋宏叫她的名字,声音飘忽如从天际传来,“今天是瑶妹纳征下聘的日子。”为了彰显对汉家子弟的礼重,拓跋宏特意准许陈留公主的婚事,按照汉家六礼的习俗操办。纳征一过,婚姻就算彻底定下来了,女方只等着礼成,便要到男方家里去了。从此是好是坏,娘家就无权过问了。
拓跋宏的语声低沉斯文,跟在明堂议事时完全不同。冯妙“嗯”了一声,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带着伤的手抑制不住地微微发抖。隔着雕镂精细的窗子,只能隐约看见他随风拂动的衣袖,看不出他今天心情是好是坏。她……很怕他。
“皇上不喜欢,”他捧起沾着泥土酒坛,凑到她面前低声说,“可是宏哥哥喜欢。”他看出冯妙的惊恐紧张,贴着她耳边柔声低语,一手捧着酒坛,一手拉过冯妙的小巧手掌,带着她专挑小路、绕来绕去,竟然穿到了碧波池边。
十月初十,陈留公主的嫁衣已经全部准备好了,高太妃不敢自己全部定下,把全套嫁裳送到奉仪殿,请太皇太后过目。冯妙提早听说,精心炖了一小盅当归乌鸡汤,估计时间差不多,亲自端了给太皇太后送去。
她的声音和着酒坛里散出的香气,一起飘散开来:“时间是个神奇的好东西,能酿出美酒,也能改变一切。我常常这样想,小时候不认得的字,现在我已经认得了,小时候拿不动的木桶,现在我也可以提得动了。所以,今天觉得难以忍受的事情,也许放在五年、十年之后再回头看,便根本算不得什么事了。”
触到她裹着棉布的小指,拓跋宏微微一滞,神情有些黯淡,却又飞快地遮掩过去。
拓跋宏捧回酒坛,一口口仰头喝下去,不再说话。冯妙抱膝坐在他对面,手指拨着鞋面上一颗滚圆的珍珠,依稀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她感觉得到,今晚拓跋宏的情绪有些不大好,似乎闷着很多话在心里,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这时距离陈留公主拓跋瑶的婚期,只剩下不到半个月,予星就算日夜赶工,也未必来得及。冯妙担心她到时交不出公主的嫁衣,等她买回丝缎来,便分了一半帮她绣。予星挑了些颜色单一、花样简单的部分给她,不想让她操劳太过www.hetushu•com•com。
徐姑姑有些为难:“这些事情,不是奴婢能做主的。崇光宫传来的口信,只说叫奴婢来教导娘娘,至于日子,怕是那边已经定下了,娘娘等着人来宣就是了。”
没过几天,尚仪局派了一名有些年纪的徐姑姑来,教导冯妙侍寝时该注意些什么。忍冬自然万分高兴,喜上眉梢地说:“娘娘晋了位分这么久,早该去服侍皇上了。”
“既然是采买的,那就好办了。”冯妙压着声音,低低地咳嗽几声,然后凝神细想,“你派信得过的小宫女,出宫去找跟嫁衣颜色相同的丝缎,不管开价多少,先买回来。这边你仍旧装作不知情,用原来的布料刺绣。等外面的丝缎买回来,要辛苦多绣一份。到了交工的日子,你就把丝缎绣成的拿出去交差,别的什么也不用再说了。”
“丝缎质地光滑,手感也好,公主身边的人原本就不知道尚工局选了什么布料,只要看到是好的,就不会说什么了。”冯妙很有把握,拓跋瑶原本就对这场婚事心灰意冷,哪里还会在意穿什么料子的嫁衣。
冯妙被他抓住手臂,阵阵发疼,可心口上一圈圈荡漾开的波纹,却比手臂上更疼。她无端地想起密室暗道里流泪的少年,不知道那是哪家的王侯子弟,说不定就是先帝的某个儿子。世人眼里的天潢贵胄,却连普通人安享的天伦之乐,都成了奢求。
“原来是这样啊,到底还是郭公公经验多些,”冯妙转身对太皇太后说,“陈留公主下嫁,事关皇室体面,为了稳妥起见,我看还是把整件嫁衣都拿到外面阳光下,仔细看看。这个侍工既然敢偷懒,说不定还有别的地方也不好,正好一起弥补,免得到时候让人挑出把柄来。也请太皇太后和太妃娘娘移步,看看嫁衣上还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冯妙手上一抖,绣针差点戳在手指上。拓跋宏一身天青色常服,正站在窗外,斑驳树影洒落在他身上,暗纹重重。
只要高太妃的口一开,予星的性命就算是捏在郭泉海手上了。冯妙站起身,做出十分焦急的样子:“处置宫女事小,陈留公主婚期马上就要到了,这嫁衣可怎么办,再重新做,恐怕来不及了呀。”
“时间已经过半,重新绣都未必来得及,”予星恨得直咬牙,“再说,公主嫁衣用的布料都是专门从宫外采买来的,现在到哪儿去找那么大幅的精细棉布。”
她把手放在妆盒上,里面装着那枚月华凝香,放的日子久了,盒盖一开,积攒的香气就飘散出来。吃下去,就永远不会有孩子,皇上可以相信她,太皇太后却不会知道。但她喜欢小孩子,她尽心尽力地照顾林琅,也有一半是这个原因。
冯妙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验证。皇帝下诏,将彭城公主改封陈留公主,食邑加倍,下嫁丹杨王世子刘承绪,准许以长公主的仪制筹备婚礼。
冯妙被连番惊吓,手指上的伤又没彻底养好,渐渐有些低热咳喘的病症发起来。和图书每天在长安殿,也有些恹恹的,精神不好。林琅原本想叫予星来陪她说话,可尚工局传回来的话却说,予星因为绣工出众,被指定了去缝制公主的嫁衣,这个月都不得闲。
竹篙一撑,小舟便往湖心荡去。
冯妙被他咬住指尖儿,半是疼半是酥|痒,禁不住轻轻呻|吟一声,低着头说:“我已经是你的妃子了。”她有时聪慧伶俐得明察秋毫,可到了这件事上,却宁愿用不懂把自己封闭起来。她不该奢求太多,没有盼望,得不到的时候就不会失望。
冯妙笑骂了她一句,撵她出去,转头有些不好意思地对那位徐姑姑说:“我近来有些咳嗽,恐怕是受了风寒,要是传染给皇上,罪过就大了。能不能……能不能等好一些了再去?”
“月亮很圆很大,我看见月亮,就走到这里来了。”拓跋宏自顾自地开口,冯妙没想到他也会说出这样带着些傻气的话来,一时又想起在崇光宫的紫檀书案上,看到的那张纸,脸颊一点一点地染上可疑的红色。
送走徐姑姑,冯妙心中越发忐忑不安。她还没想好,该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拓跋宏,他一时亲密温存,一时又残忍决绝。如果只是要讨他的欢心,那也简单,可是……
他把微热的脸,迎向微凉的夜风:“可是,我的月亮,碎了。”
予星虽然冲动愤怒,却听得进冯妙的话,也知道现在时机不利,的确动不得郭泉海,恨恨地点了点头。
“这……能行吗?”予星有些半信半疑。
“布料是采买来的,他最多不过是挑选不谨慎,”冯妙边咳嗽边慢慢地劝导,“再说,他既然有心设局害你,事前必定安排得天衣无缝,选布、裁量都叫你跟他同去。你没有办法证明,是他给布料浸泡了桃胶。其余的过错,他有多少,你便同样有多少。这件事,丝毫动摇不了他的根基。”
手指缓缓向下压,将妆盒的盖子扣拢。冯妙安慰自己,那么多人想求子都不能如愿,也许一次,并不会有什么,还是等到下次再说吧。
小舟静寂无声地浮在水面上,掌管船只的太监早已经去睡了,碧波池周围没有什么宫室,连巡夜的禁宫侍卫,也很少走到这边来。拓跋宏先跳上去,解开绳索,然后才搭着冯妙的手拉她上来。小舟轻轻摇晃,冯妙站立不稳,只能牵住他的衣袖。
冯妙心头涌起无限酸楚怜惜,鬼使神差般探身向前,环抱住他:“如果你觉得很累,挺不下去的时候,就想想很多年以后。”
假梁郡王拓跋嘉出兵淮阴,陇西公拓跋琛出兵广陵,河东公薛虎子出兵寿阳,大军同日开拔,渡江南下。原本等着看少年天子笑话的宗亲老臣,此时却恨得牙痒,他们没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有如此魄力,南征全部起用戴罪的王公或是出身低微的将领,直接绕过了手握重兵的宗室老臣。等到这些人果真得胜归来时,朝堂上的情形,就彻底不同于今日了。
“可谁知道,那布料是加过桃胶的,”予星说着就快要
和图书哭出来,“乍一看光滑致密,图样绣上去,也平整服帖。可是绣好一整幅以后,用水洗时,桃胶沾水就变软了,整幅布料都不能用了。要是到日子交不出绣好的嫁衣,我可就……”尚工局几乎忙得昏天黑地,为公主赶制嫁衣和布置新房用的布匹。
冯妙捧上还热的当归乌鸡汤,请太皇太后品尝,转眼看向那件喜庆繁复的礼服。丝缎缝制成的大红礼服,整齐叠放在彩盘里,质地光亮顺滑。一切都好像十分顺利,冯妙暗自奇怪,难道予星没有按照商量好的办法做。
拓跋宏眼中的失望一闪而过,他仰头喝干坛中的酒,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总有一天,横亘在朕面前的障碍,都不再是障碍。即使明知命运如此,朕也要走下去。”自称上一点点细微的变化,已经把他重新变成了谈笑间指点山河的帝王。
他回身问:“勰弟说你私藏了好酒,怎么给别人尝,却不给我尝?”冯妙指着他刚才站过的地方说:“哪里有什么好酒,不过是随便酿着玩的桂花酒罢了,若是皇上喜欢,嫔妾去挖一坛出来。”
她贴在予星耳边,低声说:“你在绣那幅新的丝缎时,用我以前跟你提过的那种针法,再按我说的,把那几处故意透露给你身边可疑的小宫女知道。记得,一定要分别透露,让她们每人知道的特征,各不相同,这样才好辨别。”
小舟轻轻晃动,波纹一圈圈向外扩散。
正要叫端着冠顶和礼服的宫女退下,郭泉海匆匆迈着小步,从殿外走进来,先向太皇太后叩首问安,然后才向高太妃说:“太妃娘娘,请您治老奴的罪。”高太妃一脸诧异:“这是怎么说的?陈留公主的嫁衣,全靠你亲自督造,太皇太后也很满意。”
冯妙不记得自己怎么回了华音殿,只是在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觉得头疼欲裂。那坛桂花酒埋得久了些,酒劲已经有些大,她不过喝了几口,后来竟然醉得不省人事。
“妙儿,我想要你,做我真正的妻子。”他俊朗的眉眼间,满是真诚,如同在佛寺祈愿一般。不是皇帝和妃嫔,他想要冯妙,做拓跋宏的妻子。虽然他一再提醒自己,那是冯氏送来的女孩儿,不可以亲近,甚至用那样激烈伤害她的手段,来强迫自己清醒。可心底那枝水莲早已生根发芽,不受控制地疯长起来。
“我从前读史书,最痛恨汉朝天子,要靠公主和亲来稳定西域,没想到,”拓跋宏伸手一抄,把冯妙揽在自己怀中,口中的酒气直喷到她脸上,“我竟然也要靠牺牲女人……牺牲女人来换取千秋帝业。”
予星点头答应,又有些担心地反握住她的胳膊:“你也自己小心些吧,我看你就是思虑太过了,所以身子老也不见好,比在甘织宫时还更瘦了。”
“我可以喝的。”冯妙避开他的手,嘴上说可以,脸上却泛起醉酒的酡红来。她实在没什么酒量,只一口下肚,就已经觉得身上燥热难忍,眼睛被水面上的波光晃着,有些看不清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