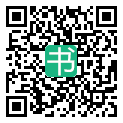卷三 雄图江山,何为欢喜
天下四
方恺口中呼喝一声,扬鞭策马随阵奔驰而去,甲片银光一晃一闪,瞬时唤回她心神。
知道了,他的事其实有那么多,她都不知道。
贺喜看她半晌却不见她开口,眸光一氲,伸手去一旁小盅里拈了几片茶叶,探过去揉开她的嘴唇,塞了三两片进去,“若是受不得羊肉膻腥之气,嚼嚼这个倒能好些。”
方恺冷眉低眼,侧身对着她,压低了声音道:“休得干涉军令!西门守军全无,南北二面未破,它内城东面纵火以诱,你知我大军进城之后不会遭伏兵来袭?!”
除却他,心与谁付?
却也不知还能说什么。
正左思右想时,腕间忽而一紧,她眸光一晃,就见他微微垂首,正在看她,大掌轻捏她的手腕,而后移下去,握住。
“愣着等死啊?!”他向她大声猛吼,手一扔缰,指向后面远处,“给老子滚回去,省得让人分心!”
英欢望着他,腕间一用力,剑锋染血,他颈间被划开一条浅口。
“自当从陛下之令。”他低头道,语气毫不犹豫。
她面如朗月初霁,稍一扬唇,轻声道:“此地山涧清泉色澈味甘,用来沏茶,正好。”
方恺眼眯人僵,缓缓半转过头,颈后冷硬之物亦随着他的动作而移至颈侧,他低眼去看,喉下一寸处,赫然正是他先前才给曾参商的那把弯刀。
八万兵阵于夜色中疾速而行,远处巍州城西高墙之上隐有亮光,纵是尚有二里亦能一眼望见。
心底蓦动愈来愈大,悄悄斜目看他,见他神色依然如常,侧脸陡峭刚硬,可手略微一动,就觉出他掌间在微微渗汗。
贺喜闻得帐外之言,眸色忽而一深,转瞬又亮,慢慢起身站稳,看她道:“三日后发兵,邺齐军中杂事亦多,便不特意抽身过帐看你了……若有它事,可来找我,或者遣人代言。”
是贺喜在为二军五将诸校誓师。
她见他转身欲走,不由起身叫住他,不放心道:“你这伤……当真无碍?”
她果真是……没用。
洪微领命而退,帐帘掀起又落,夜风顺隙扑入,险些撩灭烛焰。
她站着不动,不多时便听得山动地摇的一声呐喊杳杳传来,而后北面火星渐渐远去,几瞬之后便再也不见一丝光亮,夜尽漆黑之色。
贺喜看着她,眼中光亮迫人,似是知道她心中在想什么,下一瞬便对身后众人高声冷冷吩咐道:“留在帐中等朕。”
她朝他一笑,半侧过身子,道:“是我多虑了。你且去忙,我回帐去。”说罢便要抽手而走。
曾参商知他心生敏锐,尤是自己所道何言在他耳中都成了监军之辞,不由皱眉,道:“在下因不解才问,方将军何必出言相讽。”
她摇头,仍是笑,但见远处邰涗营帐可见,不禁一晃手腕,小声道:“你……回去罢。”
风虽不寒,可她身上竟是莫名的冷。
英欢无言,但看他利落甩帐而出,久久才坐。
她看他,手下意识地抽动了一下,却又被他握得更紧。
为狄风报血命之仇!
英欢近帐,四下打探,却不见可通传之人,迟疑了一瞬,便直直上前撩起厚帘,走了进去。
天犹未亮,却召这许多将领亲随入帐议事,这是要做什么。
帐外金铃叮叮作响,有人来禀,“陛下。”
先前见他右臂活动如常,以为他伤已好,竟不知还需日分几次换药。
分明就是骗她之辞!
她微一挑眉,竟没料到会是这答案。
她怔怔地看着眼前一切,魂魄似被抽出,思考不得动不得,如石雕一般定在马背之上。
只是他既是辨出她心已生疑,那她也便不须再多虑——
她讶然,心底蓦动。
曾参商人在马上僵了片刻,却是不怒反笑,道:“方将军滞军在此自有道理,在下不再多问将军议策。”
二日前定令那次,不知他心中还盘算了它事,怎的今夜竟像是瞒着她要行何计似的。
方恺脸一冰,定睛看过去,随即一扬嘴角,转身侧耳,半刻之后又闻身后西面隐隐传来厮杀之声,不由低声对曾参商道:“该走了。”
此次若能一举伐灭南岵残部,定当调兵北上,直捣燕朗大军一部——
他知她恨燕朗入骨,这是要替她报仇。
曾参商双手止不住地发抖,咬牙定神,对上他的眼,将长弓挎回身后,大声喊道:“方将军愣着做什么?攻城啊!”
“才知真正的沙场与你心中所想甚远?”方恺的声音自前方传来,语气略带不屑,“久居庙堂之高,对你们而言,军中士兵们的性命不过是奏报折子上的几笔数字罢了……以为这广疆阔土都是不费任何就能得来的?!”
手中盛了火油的大桶呼啦啦全翻向城头之上的守兵之中,哀号之声瞬起一片。
士兵小声道:“此事确是不知。”
方恺愣住,脸色变了变,一低头,狠啐了口,自言自语道:“也罢。”又转目看向她,咧嘴道:“城西三十里外是南岵大营,至今身后未闻战声,可见余肖一部还未袭营;城南城北尚无火光以现,是以江平、于宏两人未始攻城;待此三部先袭,南岵城内兵防势必重南北轻东西,我部才可趁势一举攻破巍州西城。”
披盔戴甲,色泽陡亮,帐中糙烛火苗跳动,映得人人脸上惊诧之情更是和*图*书诡异非常。
英欢微窘,自知白怪罪了他,心中一时惆怅,先前质问他的口气却也收不回来,只得干站在原处,半天才抬睫瞥他一眼。
他低首行礼,“陛下,”听不见英欢开口以应,不禁抬头,见她倚在案旁发愣,便又道:“陛下?”
方恺本就是吃软不吃硬的性子,听她这么一说,面上竟露出些臊色,转了头过去,自己向南望了半天,然后抬手在腰间摸了一阵儿,解下来一物,回身递与她,低声道:“喏。”
城南之向蓦然升起冲天火光,又有石落人嚎之声。
那邺齐士兵慌忙抬手压住颈侧伤口,急着往后退了两步;另一人更没料到英欢会动怒至此,虽是不解,却也不敢忤逆她,低了头也想退。
阵在前,她在后,人居于马上,心跃至城中,看油柜火箭飞至城头,火亮迫眼,满耳都是冲天厮杀之声,城周南北两面青烟滚滚,夜竟不似夜,血光染幕,一刺烫至眼底。
英欢素面斜影轻萧,抬眼对上他的目光,笑意暖融,非在怪她,不禁压低了声音轻声道:“大军南下,夜里实在清冷,心里面……”
她心里一惊,盯住那士兵,紧声追问道:“可知是去了哪里?”
他站直身子,慢慢地松开她的手,看着她,嘴角一扬,又道:“真想能一直握着你的手,再也不放。”
如此说来也是合理,倒是自己先前……莽撞了。
邺齐国之上下,内政外兵,十三年来全仗他一人扛持,该是怎样辛苦难耐,外人谁能体会得了?
方恺皱眉,低低“嗯”了一声,扯了扯掌中马缰,不语。
洪微听了微一皱眉,此二令互为矛盾,着实让他摸不着头脑,不知英欢心中究竟何意,默了半天,才应下来,“是。”
“内城东面……”她急喘,随后一顿。
贺喜敛笑,低声道:“人在军中,一向只吃两餐。”
她嘴角微垂,面上冷笑也消,猛地抬手扬剑,卡在其中一人颈间,冷冷道:“朕为二军主帅,斩你一个小卒,不需旁人来言。”
众人之间,贺喜挺挺而立,身着玄甲,臂下夹盔,盔缨白落落的,根根顺展。
万人齐动,带起风啸一片,刮得曾参商颊痛眼眯,但见人马自她身周呼行而过,如黑浪一般向西涌去,不由心起巨潮。
贺喜点头,笑意略淡,道:“只管放心去睡,二十万大军才发,最早一路也要待今日入夜后才近巍州外城,你在营中担心亦没用。”
英欢启唇吸了口山风,慢慢转身,大步走回行帐,进帐后拾了先前扔下的那书,放好,熄了外帐烛火,进内帐歇息。
他长臂撑起帐帘,笑着看她。
她猛地起身坐起,手扣在榻边,紧紧攥了一把,而后下地,飞快出帐,往东面大营走去。
疯了不成!
她心底似被人狠狠掐了一把,猛地喘过一口气,俯身便朝马下一侧呕了起来,像是要将五脏六肺全都吐出来。
方恺扭头,见她神色慌茫,驱马过来,扬手冲她坐骑之前挥了一空鞭,低喝道:“早晚都得习惯这种事,莫要于战场上露出这神色!”
满满一帐都是人。
她扔下手中薄册,去内帐中将衫裙换了,着一身绀青窄袍硬靴,也未灭帐内烛火,便快步出了帐。
曾参商一震手腕,盯着他,飞快道:“哪怕城中伏兵不可数计,你也得率军入城救火!否则,”她顿了下,眼中光芒凌厉,“我以监军之身,将你当场军法处置!”
城下邰涗士兵趁势猛推撞车,疯狂地撞向西面城门。
他蓦地笑出声来,而后沉沉一叹,牵了她的手往前走,一步连一步,奇慢,奇慢。
夜里山风轻缓,天空皓月独轮,不见星色。
一觉竟是无梦,睡得极其香甜。
倘若此次他是借伐巍之机欲图它地……
人一下子便如张弦之弓一般,心中紧不可耐。
她盯住他的眼,直截了当问他道:“到底瞒了我何事?”
英欢眼瞳一缩,眉头紧皱。
说罢,斜睨她一眼,就要驱马回至阵前。
不禁皱眉,暗叹自己心粗,伤重如彼,怎会这么快就痊愈。
…………
这才反应过来,先前差点命葬箭下。
掌中之剑砰然落地,溅起沙灰一片。
英欢手抖得握不成拳,死命咬着牙,不敢信自己听见了什么。
终究是放不下心来。
一望西面城门,守兵竟是一时全撤,方恺本欲带军追攻而入,却在见了内城大火之后,急令全军留地以待。
实在不安,难以入眠。
英欢微怔,这才发觉天已渐黑,自己竟忘了叫人燃烛,便轻点了下头,待看他走去帐角将几处高烛点了,才又道:“此次讨伐巍州南岵残部,未点京西禁军,你心中可有怨?”
英欢眼波轻转,见他一直未动碗筷,不由挑眉道:“只劝我吃,自己为何粒米不进?”
西城之上守兵果然不多,但弩兵一排排的箭雨射入邰涗阵中,马翻人落,刻刻见血。
忆起先前见他伤血泛黑,那日又被她以剑相抵、捅撞之数不知何几,抱她滚落山坡之时硬以伤臂护她周全……
英欢微微一笑,听他两句话,心便一下放了下来,道:“好。”又看了看他,缓缓转身,自向前行。
身虽未转,可其后众人皆是垂首称命,立和*图*书在原处一动不动。
另一名守兵急着叫道:“陛下!”
当是……
英欢蹙眉,又看二人几眼,其面上惶惶之色犹然未消,当是不会骗她,这话听起来确也像贺喜行事,便不再与这两个士兵为难,上前几步拾起地上落剑,冷眼冷声道:“北面若有消息传回,你二人当即时报与朕,否则莫要怪朕心狠。”
她蹙一下眉,动一下眼,弯一下唇,一举一动其间何意,他全能看懂。
她未再多言,握了剑转身,快步回营,一路脚下时重时轻,夕阳暖光铺洒而下,却是奇冷不已。
曾参商深吸一口气,垂下眼睫,手紧紧攥住马缰,心还未从先前亲手张弓射杀敌军的激震中平复下来,此时更见不得这种血飞人倒马哀嘶的景象。
贺喜眼映星光,眸色于夜下却是更黯,看着她,低声道:“午后接报,六日前邺齐大军于宾州城外遭袭,帐间几将是连夜从东赶来的。”
她垂眸,耳根又红,答不出,右手握了银箸轻轻拨着碗中的饭,却无心再吃,心底鼓动非常,声震人软。
可若不问,心中却是更疑……
这才想起他之前甲胄俱全,堂然就是一副即将率军出兵之样,可她竟被他三言二语就搅得失了神。
两个士兵互望一眼,皆垂首道:“不知。”
味道如何早已模糊,忆不起十之八九;心间惟一清明的是,初见他时的撼魄一眼,以及其后那长长久久愈酿愈醇的……缠思之情。
人行马过,噤声无言。
她转头看向帐帘,声音作冷,“何事?”
大历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二军定计合伐南岵残部;二十八日夜,帝誓师于阑仓山北,五将分领二十万兵马,南下袭巍。
一禁军士兵上前,低声礼道:“今晨,邺齐皇帝陛下抽点东面营中留守之兵八千人,出营北上,至此时犹然未归。”
此时营中才是真的全空了,人也空,心也空,思系南北两面,摇絮纷飞一般,莫论如何都定不下来。
他复又笑起来,道:“营中操练、外出行军,将兵体力过耗,我只有少进膳食,才能感同身受,知道他们能撑到何种地步,不致下发不恤之令。”
纵是得此一人,举案齐眉又将何待。
头一次,被他这样握着手,同他并肩其行。
方恺见她人已回复常态,嘴角不由一撇,直盯着她奔驰过来,却不说话。
方恺默了一瞬,低声道:“真是没用。”转身飞鞭快马便朝前冲去,口中大喊道:“中军散开待令,右翼随我一道上!”
英欢看他,水瞳凝亮,并不劝他进食,只点点头,轻轻道:“知道了。”
五更已过,人竟是一丝睡意都无。
八万兵马瞬时如石断水一般分裂成十阵,由各将校带了,分开朝西城高墙火亮之处疾行而去。
曾参商收好那弯刀,淡笑一下,并未多言。
抬眼就见方恺脸上染了血灰之色,眼中怒火似要将她烧透。
京西禁军上将下兵,对她礼敬之数自非东路大军可比;此次两军合伐巍州,方恺因洪微麾下人马未曾经战,便留京西五千禁军于大营中,一兵一卒都未调用,而洪微自始自终也未说过什么,尤是令到既行,毫无怨言。
二人停下,对望一眼,僵然不敢动。
非见他一眼不可,否则心不能安。
铁甲似浪而动,人马若洪前淌。
她垂睫略算,待斥候快马回营以报之时,中宛大军当是更近,难怪他要连夜布议出兵,口中不由又问道:“邺齐八千兵马发往何处?”
她起身下案,走至他身前,定望着他,低声道:“你出兵北上,沿向登州一路派探马索寻邺齐大军之迹,若遇之,则传朕口谕,拦其不得北进。”
虽是那般低深沉挚,然到底……能不能信他。
她慌慌忙转过身子,待心中狂起之澜小了些,才又回头,看他道:“宾州之事若有变数,莫要瞒我。”
英欢目光转寰一方,邺齐中军大帐周围仍无守卫,忆起先前帐中几人之前在帐外似是见过,想来当是夜深营空无人扰,才被他叫入帐去的。
贺喜用力一握她的手,低声问她道:“笑什么?”
她心间飞滚万念,急着想要寻个正经说辞以应,却看见他笑意深深,绕过帅案,朝她走来。
声如洪涛,响震耳骨。
曾参商挑眉,伸手接过,夜色之下看不甚清,隐约可辨得是把弯刀,不由握住刀柄一抽,刃光亮眼,她抬头,笑道:“是把好刀。”
他笑意正浓,望着她的目光颇能溺人。
伏在马背上动不了。
方恺咬牙,右臂猛地竖起手中长枪,大声怒喝道:“攻!”
洪微人至之时,正是夕阳全落之景,天际并未全黑,却是灰蒙蒙一片,行帐中光影黯淡,并未燃烛。
风簌簌扫帐而过,此夜冷甚前一夜。
偏他一副万事不摧,铁骨铮铮之样,纵是身伤体疲,也作云淡风轻之态。
洪微摇了摇头,恭敬道:“臣断不敢有怨。”
曾参商脑中飞翻乱转,心中之前阴霾如被风扫,一时尽抛脑后,只顾急急整甲正身,而后策马冲将过去,口中大喊:“方将军!”
洪微上前,迟疑道:“陛下,可须臣点几支帐烛?”
耳膜颤颤,远处高喝甲震之声随风飘过来时已淡得听不清。
左翼骑兵和图书闻言皆握紧了手中槊戈,看向城门口的刀车时眼底均是血红一片,听得将令,齐齐高吼出声:“冲!”
两列前锋步兵疾速将撞车撤走。
不是泪。
那小兵以为她是不满他之所言,慌忙又接道:“皇上今日抽点营中八千人马,亲率大军北上,意在阻其所进。”
士兵摇头,握戟道:“问过东面营中的守兵,却道圣意不可泄,又道昨夜里陛下去过东面大营,当是早已知晓。”
洪微再点头,“是。”
可他先前分明说过,邺齐军中此次只有余肖、江平二将,现下当已领兵直扑南面巍州,可为何——
她横眉冷眼一望远方城墙,猛地一抽马臀,紧跟其后,疾速而行。
帐外人行马疾,踏飞营道尘土一片,灰入青夜,人在营中都能感到脚下隐隐在震。
她微异,纤眉挑得愈发高了,“为何?”
三更造饭,五更出兵。
最前面的邰涗士兵们跃马而下,一列将倒一列又上,数人手持长枪聚于一处,拼命狠顶刀车无刃之处,以血肉之躯生生冲开一路。
想起那一日在她行帐中,他揽着她,低声道,终此一生,定不负你所信。
不知过了多久,帐外天色是一夜最黑之时,心始终还是落不至底,在胸腔内忽上忽下地跳个不停,愈发紧张不安。
方恺回首,双眸漆黑如夜,抿着唇盯了她一阵儿,才一扯嘴,轻嗤一声:“曾大人难道是怕方某临阵不战?”
奇痒奇麻,她心底一酥,驳不出口,夜色掩了她面上绽红之容,半晌才一点头,轻声道:“只得到两营相汇之处,不得叫邰涗营中守兵瞧见了。”
二人忙点头,“遵陛下之令。”
英欢忽而回神,眯了眼去看,见是他,随意一挥袖,道:“虚礼免了,过来些。”
不禁又犹疑起来,心中更是忽上忽下,定不下来。
燕朗之部,中宛大军五万,他竟敢只抽八千兵马便北上阻援——
…………
十步之后忍不住又回头看,恰见他才转身,大步飞扬往回走去,身上玄甲色泛鸦青,一路渐渐隐入夜色当中。
知他统军带兵定非闲适之君,却未料到他拥一国之重,却对自己如此苛责。
“站住。”英欢眼底血红,声音寒渗骨髓。
英欢缓过盛怒之火,慢声问他二人道:“昨日接报时,中宛大军行至何处?”说完,又挑眉望了眼地上落剑。
褐眸温光撩人,刀唇薄刃犹利。
英欢看他,轻浅一笑,“去罢。”
这一生能这样唤她、敢这样唤她、愿这样唤她的,不过这一人。
二里之距,眨眼之间便至城下。
直到再也看不见。
还未反应过来时,手中马缰便被人狠狠一拉,人马转了个圈,朝向后面。
抬手去一旁瓷盅里拈了几片茶叶出来,放在掌间,慢慢地捻了又捻。
被胁那人脸色僵白,颤着道:“回陛下的话,昨日接北面来报,中宛燕朗一部派兵五万南下,像是先得二军伐巍之策,欲解巍州之急。”
她胸口似被石车碾过一般,从未料到战场之象竟是这般惨烈,血肉扑飞之际她几将窒息,只拼命地拽稳了身下马缰才定住了身子。
浓浓讽意,外加不屑之情,她就是傻子也能听出他话中之意。
英欢眼眶忽而凝泪,自己也不知是怎么了,不过闻得他这带笑一言,竟是比生离死别还让人揪心。
她默不作声地嚼了几下,茶叶涩香渐溢,口中异味一时尽消。
锋刃利亮,映着远处城中越燃越熊烈的火光。
头顶星转夜移,天际隐隐泛白。
后面人马轰然踏尸以入,拼将砍刺城门内侧南岵守兵。
仍有几人着了将甲,站在他身侧。
那小兵未料到她会这般冷戾,一时抖起来,却仍道:“……真的不知。”
曾参商凝眉看他。
英欢冷笑,“朕知道他不在,”她抬眼看看这两人,辨出是昨夜在中军大帐中是见过的,不由紧紧一攥剑柄,沉声道:“邺齐守营之兵,八千人马去了何处?”
英欢听了,一时更是窘迫万分,脸上虽作冷色,手心里却渗出几粒汗。
守卫在帐外低声道:“东面营中来人,说是随驾医官,欲请邺齐皇帝陛下回帐换药。”
英欢晗首,又叮嘱一句:“北面若有动静,随时派人回营以报,万不能耽搁。”
方恺半侧了脸,慢慢道:“你那长弓,趁早别用,免得添乱。”他停了停,又斜眸瞥她一眼,补道:“给你这刀可不是让你陷阵杀敌的,防身而已。”
心中虽疑,欲开口相问,可邺齐军政大事又岂是她疑涉得了的。
余生尽耗,只想同她在一起。
他停下,转身对她,低下头凑近她的脸,道:“其实我不怕叫他们看见。”而后笑了一下,笑中深意她一眼既明。
曾参商见他这神色,想见当是同她想的一样——巍州内城东面乃邵定易所居之处,从南岵宫中封桩库携至中宛的残财也尽数屯于那里,此时东面起火,莫不是邵定易又要弃城以逃,宁可烧毁大量财物,也不肯叫邺齐邰涗占了去!
洪微虽面露诧色,却仍道:“是。”
莫论天子之尊,便是寻常将领,又有几人能做到像他这般!
难得一享他之温柔,然似今日这般共坐与食、相谐以对,往后又能得几次。
鬓边一声利耳之音,颊侧火
和_图_书辣辣的痛。又有一排厚甲之卒从城墙上往下倒浇火油,其间还有碎石一并溅落。
英欢蓦然转身,眉尖攒紧,见他下巴微仰,正望天上繁星,容思淡漠、波澜丝毫不起,仿若先前之事如烟既过,并无被他搁在心上。
“信我。”他头又低下来些,对她道,声音缓而稳。
五千人马可谓杯水车薪,然聊胜于无,她倾己之力,所能做的不过这些而已。
右面那人辨出她眼中何意,忙道:“五万人马将过登州,距阑仓山北尚有三百里。”
撞车由两列前锋阵猛地推向巍州外城西门,随着士兵们的震天呐喊声,一下下地冲撞着厚重打卯城门。
后颈处忽而一冰。
怕是此言说出去,天下也没几人肯信。
内城东面红光耀夜,火势凶猛无比。
贺喜看着她,顺口一道:“以为你早就睡了。”
方恺似笑非笑看她两眼,慢慢又道:“不过曾大人本也就不懂兵事,虽为监军亦不必上阵以战,既如此,还是回阵后去罢,免得到时刀枪无眼,伤了大人分毫。”
须知此次二国合军共伐,邰涗意在囚人,而邺齐旨在夺财,倘是邰涗大军眼睁睁看着封桩库被火烧毁而不入城施阻,那负责牵制南岵城西大营、以便方恺之部能顺利攻破西城的七万邺齐大军又怎会罢休,而两军之间又会成何局面!
一入帐便叫人传此次统京西五千禁军护驾至此的洪微过帐见驾。
她不禁一急,怒道:“方将军既是明白,为何还不叫大军入城救火?!”
随一声尖啸,左前方马阵侧翼飞速驰向巍州西城之门,一路之上火箭犹然未灭,焦黑之血粘稠不堪,马蹄染血踏火,冲向城门之速锐不可当。
乾乾苍穹夜下,两军大营之中,他就这般旁若无人、毫不顾忌、光明正大地握住她的手,不放。
身边空空之时,心中可偎之人,只有他。
她冷眼一扫,“说不说?”
醒来时日已西落,于远处阑仓山巅衔了道火红金茫,烫眼烫心。
贺喜薄唇弯了一下,之前甫一见她入帐时的惊诧之色已收,右手抬起,在寒砺案沿上轻轻一敲。
原来心中紧动、情思翻涌之人,不独是她。
自己不顾礼数地闯进邺齐中军大帐中,扰了他的正事,众将齐对、待她开口,可她又不知该说什么。
一路疾行,东面竟是静得诡异,往常两营相汇处的邺齐守兵也不见,看见远处中军大帐中隐隐透光,才知他人已归帐。
合营之处有两个邺齐士兵,见她过营忙上前相拦,道:“陛下,皇上不在营中……”
帅案被移置帐间,其上罩了张油布,布上铺了一大张透光薄牛皮。
贺喜牵住她的手指,前迈一步,低笑道:“我送你回去。”粗糙长指轻轻揉搓了她的手心一下。
五支利箭齐齐射向城头,一箭一中,五人倒下。
经历过太多残伐、猜忌与峙难,点蜜也成一番冷。
曾参商慢慢抬手,抹了把嘴,眼里滑出一粒水,顺甲而落。
伐巍之令乃他所定,虽说方恺服之无异,可邰涗营中兵马倾巢已出,邺齐大营却仍留了他一万亲军——
曾参商默然半晌,轻一点头,道:“有理。”她看向他,笑了笑,“在下初随军行,还望方将军往后不吝赐教。”
当日因茶识他;其后他辗转两将之手送与她的那一小瓶蒙顶甘露,她不过只在那一夜饮过一回而已。
只是因身子太难受才……
他深知她在想什么。
她先前只见那牛皮上绘了图字,因站得远,并未看清其上究竟何物,此时待那小将收卷时再一瞥,隐见像是地图。
她怒火中烧,一脚踢飞地上之剑,心底一阵阵地抽痛……她不需他这般为了她,以命相搏!
轰轰战声无休无止,将她耳膜震得僵痛万分。
她掀睫,望进他笑意满注的双眼,脑中闪过那色碧毫卷的茶针,不由轻叹,“那蒙顶茶……”
英欢一时火起,一把抽过那士兵腰间佩剑,冷眼一瞥,再未多言,转身飞快便往东面营中走去。
英欢僵了半瞬,突然莫名一笑,不过短短三日而已,便从他口中听得两次似诺之言,她与他之间的那根坦信之梁,当真是危且脆。
听着外面营中士兵们低语喧哗声渐渐小了,战马蹄踏营道之声答答作响,才知上将下兵都已吃过饭,将开始整军。
将近城门那一刹,城门陡然自内大开,两架白刃数插、狰狞似兽的刀车被南岵守城之兵疾速推出。
贺喜过案之时侧目看了一眼身旁小将,那小将顿悟似的,立时上前去将案上那张薄牛皮卷起来。
为帝十三年,第一次御驾出征在外,第一次亲睹大军开拔,第一次知道纵是徒守帷幄亦非易事。
气如风扬,士不惧死。
英欢唇微扬,目光带了嘉许之意,轻声道:“倘若朕此时有事托嘱你,需你出兵以任,你可愿意?”
欢若平生。
头虽低着,心虽颤着,但城中突起冲天火光一片时,她却猛地撑起身子,抬头望去。
她蹙眉,转眼去看他。
蒙顶天家贡品,千金难求半两。
方恺眯了眯眼,忽而伸手拨弄了一下她身侧长弓,挑眉道:“攻城之战,此物多余。”
他望着她轻开轻合的红唇,半晌才挪开眼,笑道:“才想起,我帐中还有hetushu•com.com些许蒙顶甘露,你若想要,我遣人给你送来。”
她呕得眼里都要滴出水来,头昏身软,手撑在马鞍上,抖得不能自持。
猛地策马至阵前,高声喝令麾下诸营都指挥使,分兵全速向巍州西城进发。
曾参商看着眼前血幕战景,嘴唇都在哆嗦,手紧紧攥着身下马缰,万没料到方恺会下如此狠令,而邰涗士兵们竟是如此不惜己命——
只为一胜!
一看便知是集将议事之景。
空敞敞的大营间甚是清冷,只有北面远处传来的错甲之声漾起一丝生气。
他回头,冲她抬抬右手,笑得直侵人心,“当真无碍。”
外面夜已全黑,如炭似墨,黯无月星。
半步将入,抬眼看清里间之象,人一下子生生愣住。
昨夜所道宾州大军遭袭——
曾参商驱马上前,至方恺身侧,斜眉以望,低声道:“方将军为何叫大军停下?”
兵事之惨烈,人命如蝼蚁……
英欢目光扫至左面那人身上,盯着他压于颈侧的手,唇一冷扬,“当真不知?”
她心中如鼓在震,恨火飞窜,抬头朝远处高耸城墙上望去,伸手一把扯过身上长弓,又抽出五支箭,猛地张弓,将五支白羽横镞利箭一口气全搭于弦上,而后定睛朝城头火光望了一瞬,右臂一震,指松箭发。
他嘴角纹痕刺眼,半晌又道:“此事乃邺齐军机要密,未与你提也算不得什么,况且今夜发兵巍州,又不得让营中将兵知晓此事,以免乱军心挫士气。本以为你入夜后便歇息了,未曾想到你竟会找来。”
方恺身上银甲之光于阵中甚是醒目,臂夹长枪,待人马又行一刻之时,忽而转身传令止军不进。
……当真是进退维谷。
英欢人怔心僵,抬眼便去看他右肩。
兵马一波波停漾止住,黑压压覆于巍州城外广袤之原上。
她垂首,笑容瞬时皆消。
他不怕,但是他知她怕。
足下由是更僵,不明他要做什么。
干燥骨硬,有力而又温暖。
英欢微低了眼,看着足下淡影,二人步子相谐,身形相偎,般配万分。
喜欢的罢。
蹄踏风动人如剑,二十万大军齐齐将发!
英欢兀自僵在帐口,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任帐中诸人肆无忌惮地打量她,自己飞快一扫帐内诸人。
还未来得及细想,睫转一瞬,他人便至身前。
只一瞬,就见前方血溅七尺,战马遇刀而翻,士兵滚马落地,甲盔触地之声纷纷不休,打头阵欲破城而入的左翼骑兵损一折二,后面数千人马立时止步不进。
英欢心中又虑,以贺喜之雷行之风,莫论此时派兵还能否追寻得到,便是追上了,恐怕洪微也拦他不下,不由又道:“若是邺齐大军一意北进,你便领兵与其同进退,只道是朕遣派你去的,一切都听邺齐皇帝陛下之令。”
星光萃灿,悬冷清辉,苍凉夜幕缀石朵朵,浅风非疾却侵人。
她想要冷笑,可人却僵乏难耐,脸上连一丝生色都作不出,眼前血幕片片,又想起狄风战死的那个梦。
他无声而笑,嘴角令纹深深。
英欢夜未入眠,独自在帐中映烛而思,时不时地拿錾花铜细挑挑烛芯,心不在焉地盯着手中书卷。
这番乱糟糟一搅,心中之前因徒留空营的紧张和忐忑之情顿时全无。
曾参商闻言蓦然抬头,竟不敢信。
不由轻笑。
英欢抬手一把推开他的掌,水弯长睫轻抖,瞪他一眼,佯怒道:“成何体统。”
相斗相识,相念相爱,天下万万人,惟他能知她心。
帐中其余人等瞬时回过神来,纷纷低头顿甲,向英欢齐声道:“陛下。”
贺喜眸深人顿,半晌又道:“算不得什么事,你……”
曾参商恍然回神,抬手飞快一抹脸侧,见沾了点血,幸而那箭只是划破了脸上一点皮,足底一硬,转眸就见方恺带怒策马回阵。
方恺飞快转身,望见城门已开一缝,立时冲骑阵左翼狂吼一声,令其入城以攻。
城门裂缝将开之时,方恺蓦然于阵中转身,回首望向她,纵是隔了这么远,他那眸光也要比身后火光更亮数分。
那人脸色早已僵白似纸,低头低眼飞快道:“当真不知。皇上率军令出无定,常是人于阵中定令以发;因是只知兵马离营赴北,不知圣心何向。”
她会意,垂睫转身,轻步出帐,身后男人跟着出来,帐帘重落。
“世间体统……”贺喜低笑,好整以暇地丢下绸帕,以手撑膝,望她道:“你不喜欢?”
英欢拢衣出帐,吸几口外面山间清风,心情顿好,欲叫人传膳之时却见几个守卫神色均是古怪,不由蹙眉道:“怎么?”
难怪不愿告诉她,宁可骗她也要瞒她。
不想再看他一人独自扛下那种种之难,纵是不能替他分愁,亦不想被他次次隐瞒。
多年相峙相对互相猜忌,此时忆起他那满腹心机狠辣手段,不由猛地升起一念。
指腹轻扫过她的唇,心水汪涌。
玄甲冷戾,昂藏七尺之身恰将身后众人的目光替她遮去。
她转身朝北看过去,两军千帐连之不尽,帐角如雨线一般,一路没入漆黑夜色当中,只有极尽目力所望之处可见有点点火星。
并未宽衣,就这么躺在榻上,靴底一下下磕着榻侧木缘,弹指算着时间。
令自上出,他谨奉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