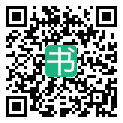卷二 欢若平生,喜之不尽
帝业十三
英俪芹被他的力道压得几要喘不过气来,泪止也止不住,看向他的目光且怨且愤。
沈无尘立在殿中,心沉沉在跳,此知遇之恩,君臣相得之情,便是付此一生,他亦甘为她脚下栋石!
曾参商脸色臊红,又要去抢,却被他错开,听见他道:“既然写了,难得一见你之所作,不管是什么,我都得仔细读一读才是。”
是气自己这回竟将输给她。
“臣明白了。”隔了良久,他才慢慢道,语气归了往日之稳若淡然。
沈无尘近案五步,跪拜叩首,“臣恭请陛下圣安。”
待那宫人走近,他才快行几步,随那人转身往景欢殿行去,随口问道:“皇上一直未睡?”
沈无尘点头,“陛下的意思,想必他是清楚的。坐山观虎斗,北戬何乐而不为之?况且,陛下本就倾向于天下三分而非两治,他又怎会不明白臣此行的深意……”
自己不是能为了女子而扬袖弃走庙堂之人,否则也不会因她而动情。
十月初四,南岵大军弃潭州,北上至梁州以西阻狄风之部,朱雄占潭州后疾行北上,又破魏州、晋州、绛州。
……当是不肯。
宫人在前与殿前候着的俩人低语几句,而后轻推殿门,转身唤他,“沈大人?”
贺喜正要发作,就听殿门又是一开一合,回头便见谢明远已然进来,黑袍黑靴一身爽利,只是面色不佳。
“时已入夜,为何还留在户部不走?”
可,知虽已知,臣子之责却无法改。
帝后不和,宫中人人皆是有所耳闻,可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皇上得知皇后有孕,竟也能动这么大的怒。
“陛下……”他急急道,“臣资历尚浅,怕是难以担此重任。”
等她……等她什么?
沈无尘一把抓起她的手,用力掰开她握紧的指,低声道:“都敢这样写了,还不敢这样叫?都已成此情态,你还想……骗自己多久?”
英俪芹闻言,头一下便晕起来,眼角又沁出几颗泪,“你不如干脆杀了我,一了百了!”
册后至今九月有余,贺喜只在邰涗皇帝陛下大婚那一夜来过宣辰殿一次,而且只待了不到半个时辰便走,并未留宿,自那之后的七个月以来更是从来不近宣辰殿一带,今日突闻皇后有孕,旁人心不起疑,他却是着实被撼!
曾参商低着头,左手掐着右手,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
“参商。”他低声唤她的名字,又将她的手握得紧了些。
英欢起身,绕案下阶,纤眉尾扬,眼里浅光微漾,“十二年来你政绩斐然,朝野中人有目共睹。虽未外放出任大郡知府,但奉旨出巡之事亦不在少数。此次着你出使北戬,你领命稳而不惧,行事进退自明,颇有担当大任之范,廖峻已在朕跟前赞过你多次……”
英欢轻扬手中薄折,“这是你人在北戬时发回来的,后面可还有变数?”
英欢望他半晌,眉眼之间一片清冷,“出了这殿门,此话休对旁人道!”
他哪里有资格去要求她为了他做什么,又凭什么以为自己一定就是她心中那一人。
英俪芹费力撑坐起身,去推贺喜,人已哭得不能自禁,“你杀了我,你干脆就杀了我罢,莫要连累旁人……”
沈无尘陡然回神,忙将身上常服整理一番,而后提步入殿。
“外城禁卫一路上奏,禀至天听还需一阵儿,所以就过来先看看你。”他抬起胳膊,迟疑了一瞬,仍是伸过去,握住她垂在身侧的手。
“俱在外殿候陛下圣驾。”宫女敬道。
宫人几要小跑才能跟上他的步子,明明是秋风乍作的天气,却是满额的汗粒,嘴动了又动,才嗫喏道:“太医说,皇后是有孕了……”
他在座上不语,底下诸臣心中更是没底,不知圣心究竟何意。
众臣默然,深知他的脾性,也便不再相劝,鱼贯退殿而出。
“陛下。”
贺喜一听她口中旧称都出来了,不由更是恼怒,先前好容易压下去的火一瞬间又扑燃而起,上前将那宫女从英俪芹身边拉开来,甩至一旁地上,厉声道:“你既是日夜不离侍候皇后,想必定是事事俱明。皇后不肯开口,那么你便替她说!”
贺喜深吸一口气,握拳于身后,转身绕柱,朝殿后行去,才出去便见有宫人候在外面,一副焦急神色。
李杜二人相视一番,虽是不知贺喜因何而怒,去也不敢不遵,诺诺而退,出去后又小心翼翼地将殿门掩上。
沈无尘喉头似是被什么卡住,一个字也道不出来。
沈无尘仍是将那纸高高举在手中,眯了眼看过去,口中轻声念道:“……讳无尘,字子旷,为沈氏。”蓦地挑眉低眼望她,“这是……”
她哪里能担负得起他这一番情,位尊身贵者似他,又能等得了她几时?
沈无尘步子更大了些,今日之事在他入城之后听人略略提起过一些,心中也是大悦,只是一想到千里之外的狄风,又不禁有些担忧。
不必沈无尘说她也能想到,这天底下谁还能比那人更了解她,而他又怎会看她翻手动腕而坐视不管。
曾参商面上心中皆是火,连指尖都要羞红了,伸手扯过那张纸,迅速将它撕碎,又将纸屑紧紧攥在手心里,“沈大人还真是……”
“陛下……”座下有人轻声唤他。
沈无尘挑眉,朝后退了一步,将手举高,抬眼去看,薄薄宣纸透光而亮,其上小纂字体灵秀中又带了野气。
她站在原地,手心里凉凉的一片汗,看他转身,看他推门而出,看他的背影渐移渐远,慢慢隐入浓浓的夜色中……自己深吸一口气,抬手揉了揉泛红的眼https://m.hetushu.com.com眶,退了几步,靠上身后案台。
她心里轻轻一叹,二人相隔万里之远,中无言辞相传以达意,那人竟也能知她心底之意,当真是……
本是丝毫没挂在心上,满脑都是西面战事,一入凝晖殿便把此事抛在了脑后,此时乍一听这宫人来禀,心中竟觉厌烦。
八月二十六日,邺齐大将胡义自北梁道出兵,直取中宛东境重镇云州,又连下随州、复州、新州、荆州。
他眸光若萃灿星河,动作矜慢,松了她的手去揽她的腰,缓缓吮吸她的唇瓣,未闭之眼满绽笑意。
沈无尘跪着,眼望前方龙案角座,“戌时一刻。”
曾参商蓦地抬眼看过去,一袭青衫端端映入眼底,门边男子甚是俊朗,正嘴角压笑,盯着她瞧。
南岵五十八州,至此时此刻,邰涗占二十九州,邺齐占十八州,梁州南北尚有十一州悬而待破。
还未至门边时,身后便传来他低沉压抑的大笑声,她忍不住又转身,见他笑得眼角都皱了起来,捏着那纸的手也在晃抖,不由更气,“不许笑!”
在世为人三十二年矣,终不知自己会有这么一日。
俩人之间气温陡升,他掌心热度似文火淡燃,虽非炙热难耐,可却异常撩人。
小宫女眼中俱是泪,手将裙侧捏得紧紧的,仍是一字不发,目光越过贺喜,看向谢明远。
英欢停了半晌不言语,任他跪行大礼,良久才又道:“先前做什么去了?”
曾参商支肘于案上,小脸被烛光映得一片昏黄,眉毛挑起,抿着唇盯着眼前一纸白宣,一动不动。
英欢扬袖,免了他跪谢之礼,眼中之光愈亮,将他左右打量一番,浅笑渐凝,开口时声音低且稳:“邰涗自太祖开国至今,三十二岁便拜相者,惟卿一人耳。”
英欢脸色瞬时黑了,想也未想便开口,沉沉吐出几个字:“你做梦。”
英欢不禁挑眉,诧然相望。
贺喜嘴角僵了半晌,行进间抬手将身上龙袍前襟扯了扯,忽而回头对那宫人道:“你去嘉宁殿找王如海,传朕的口谕,叫他带上起居注来宣辰殿候驾。”
英欢走近他,“你沈无尘还有怕的事情?”盯住他的眼,“只不过,朕亦在犹豫,不知若是拜你为相,你会不会比那些老臣们更让朕头疼……”
沈无尘微微笑着朝她走过来,低头去看案上那纸,“不是说再也不作文章了么?”说着,伸手便要去拿。
难亦难,苦亦苦。
贺喜手指骨节僵硬,沿着图上墨线缓缓描画,眼底愈黑,面色愈冷。
虽是问话,可却不等她答,他便目光飞移而视,又继续念道:“……子旷为人,外虽愉恬,中自刻苦,而志守端直,临事敢决。进,足以傲视群雄;退,亦可宠辱不惊……”
如是也罢。
床塌边的碧丝青纱帐微动一下,卧在里面的英俪芹听见声音,想要起身,却被在旁侍候的宫女挡了下来,“太医说了,皇后需得卧榻休养……”
贺喜左臂一抬,要过起居注,垂眼匆匆翻过,自其间猛地撕下一页来,揉碎之后又将其扔还给王如海,“补上,三月前今日,朕宿于宣辰殿。”
贺喜瞥他一眼,兀自起身,眉间成一个深深的川字,漠然道:“容朕再想想,待明日再发诏与朱雄。”
“臣不求金钱赏赐,惟有一愿,还望陛下成全。”他开口,声音低低,语气坚定。
曾参商本是气他,可听见他那最后一字,喉头竟是瞬间哽住,眼眶一红,隔了半天才道:“你一走便杳无音讯,我还以为你真的……”
狄风的性子,向来是报喜不报忧,八年前一次他身负重伤,性命悬于旦夕之间,京中却是三月后才得以闻之,时他已率军而归,回京之后也只是云淡风轻地一语代过。
“唤我子旷。”沈无尘眸中凝亮,盯着她道。
惟卿……一人耳。
那宫人止了步子,嘴唇动动,小声道:“陛下忘了,起居注现下已不归王公公管了……”
…………
与那一日在秘书省后墙外时大不相同,这个吻全无当日|逼迫戏谑之感,轻且温柔,慢却热情。
邰涗虽与邺齐缔盟,此次又是联手共伐南岵,可单单一个梁州便让两国大军互不相让,可以想见若是将来南岵既下,二国抢攻中宛会是怎样争伐掠地的局面。
沈无尘胸口之血沸涌,望着她,便要跪拜谢恩,却为她所止。
她脸上笑意淡了些,“说。”
沈无尘松开她的胳膊,目光将那纸上下扫落一番,挑眉轻念道:“……大历元年举进士,第一人及第,历大理评事,著作佐郎,太常丞……张文靖公、谢敏公、与今参知政事廖公,咸荐其能,改右司谏,太常少卿,秘书监,吏部侍郎,左丞,就拜工部尚书。”
曾参商抬眼瞪住他,张口便要骂,可未吐一字,就见他双眸一黯,按在她唇上的手指已探了进来,轻轻捏住她的舌尖,而后缓缓捻动了几下。
贺喜看向王如海,语气甚是不耐,“朕让你补,还有什么可多问的?”又转而朝英俪芹看去,冷言冷语道:“莫以为朕是为了你。护你名声、保你后位,不过是因二国之穆。”
贺喜脚下骤停,猛地回头盯住他,“再说一遍!”
只是眼下他已知,情苦为最苦,倘是他身处英欢之位,身陷她之情境,怕是不及她之万一……
两相取舍,究竟选甚。
贺喜起身,沉了眉头,对王如海道:“平日里六尚局的女官是用什么法子整治下面那些不老实的宫女的,你去弄一副来,莫要叫太医院https://m.hetushu.com.com的人知晓。”
英俪芹唇上血色全无,抿紧了唇,头偏至一边,怎么都不说话。
“还未。”沈无尘微笑,“本是说明日午后才到的,可一路上出奇地顺,入夜未久便至城外。”
她心底悸动愈大,头一回听见他这样叫她,可却无一丝不契之感,好像这语气这声音,早就植入心间,他就该这般唤她。
英俪芹身子轻颤,眼睫一落,便有泪珠滚下来,“陛下……”
燕平宫中,凝晖殿内满满重臣,却是一片死寂,殿中气氛诡异万分。
外面恰时响起王如海的叩殿之声,“陛下,小臣将起居注带来了……”
即使听见她出言以驳,他仍是不愿就这么放弃。
只是终究无法将自己心中之情淡漠视之,助她就意味着得不到她,若想得到她,便只得砍断她胸中之志。
中宛因先前集结兵力西抗邰涗,东面损了五州与邺齐,而邰涗只在得了西面二州后,便按兵不动。
王如海捧了册卷进来,面上亦是沉肃有加,待入得内殿,看见里间情境,心中顿时明了七八分。
狄风之部已近梁州以西不到百里,而朱雄麾下邺齐大军却被大雨困在苍峡一带,前方仍有四镇未取!
“廖峻举荐了你,其他人也是此意。”英欢打断他,不紧不慢地道。
冷汗沾满袍背,宫人忙不迭地点头遵旨,看着贺喜转身大步而去,这才退了,往嘉宁殿那边去了。
英欢垂了眼,手指绕与袖口金苏,不再开口。
他目光扫过她的脸,自嘲一笑,“明知你不会放弃现在的一切,我却还想要你和我在一起。明知你同她一样,是个不会因男人而不顾己志的人,我却还想让你离了这朝堂,只留在我身边。”
沈无尘脑中轰地一声,血液冲顶,似是不信自己听见了什么,“……陛下是说……?”
他自贺喜尚是皇子时便一直近身侍候,现如今总领大内事务,这么多年来宫中再无人能比他更了解贺喜的性子,贺喜每日起居临幸引见诸事,他皆是事无巨细亲躬而为,大小之事,从无一事能瞒得过他。
沈无尘看她一眼,迈了几大步走过来,飞快地将门板合上,然后将她拉至身边,抬手揉了揉她束好的发,笑道:“我没日没夜地往回赶,只想能早些见到你,你却躲在此处,给我作墓志铭……”他扬了扬手中薄纸,眉清目明,“就这么想让我死?”
谢明远低垂了头,半晌才道:“臣不知。”
英欢气消大半,瞥他一眼,“起来说话。”待他起身站稳后,才又道:“姚越年前重病,几个月来迟迟未好,因年老体迈不堪朝政重苛,几日前刚递了以病致仕的折子上来。”
古钦见宋沐之讪讪而退,想了一想,也上前道:“陛下,就算南岵梁州未夺,还有中宛吴州可取。眼下邺齐在中宛之势强过邰涗许多,将来势必能将于南岵所失之利在中宛讨回来。”
贺喜松手,眼中冰气渗人,“杀你容易,但朕若杀了你,邺齐同邰涗之间又将成何局面?”他将手背上的湿泪在被面上蹭去,再开口时怒气更大,“朕再问你一次,你说是不说?”
其实心中早已知晓是这结果,可还是不甘心。
曾参商咬着嘴唇,撇开眼不看他,心却越跳越快,好似秘密被人窥觑到一般,只想转身就逃。
沈无尘履踏御街青石砖,嘴角笑容渐淡,手握了又握,眉锁心沉。
奢念,终究是奢念。
沈无尘抬头朝英欢看去,见她面色如常,更加不明所以,不由道:“臣不知陛下何意,此等大事,当咨二省老臣……”
沈无尘攥紧了拳,“望陛下赐婚一桩。”
沈无尘低头看她的眼睛,“我等你,好不好?”
若说这天下有人能让曾参商放弃己志,那人只能是她。
她抬头看他,心中仍气,咬着嘴唇不说话。
贺喜攥攥拳,“你们都在外面候着,未闻诏传,不得入内!”说罢,大步而上,过槛入殿,而后自己扬手一把将殿门摔上,震响惊心。
胸怀霸图之志似贺喜者,又怎会看邰涗日渐独大,那男人恨不能将她同天下一并纳入怀中,又怎会忍得了永不打邰涗的念头。
多年来几国相持相衡,此局一旦被破,若是南北中三国俱灭,将来邰涗又将拿何制衡邺齐滚滚雄心。
贺喜大步往前走,冷着脸对那宫人道:“太医怎么说?”
八月二十日,于宏破顺州,中宛不敌西面重压,自东调兵西进,以御邰涗之犯。
脚下宫砖上落叶满铺,每一步下去都有枯叶被碾碎的轻微之音,黄中泛红的叶脉筋筋断裂,远处天际乌云蔽日,秋风卷起一片灰。
小宫女倔强扭头,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死咬着唇不吭声。
他的声音低低沉沉,稳而不躁,几句话字字清晰,好似是在心中埋藏已久,就待此时道出。
贺喜冷眼瞥过去,“朕怎会不知?逞你话多!且去办好吩咐你的事,旁的莫问!”
英欢蓦地打断他,声音更冷,讽笑道:“朝中多少年就只见她一人,她有多努力你不是不知道,朕想问问,你沈无尘凭什么能让她为了你而放弃现下的一切?朕还想问问,若是让你为了她而抛却身上尊位,你肯是不肯?”
沈无尘沉眉不语,不知英欢为何要同他说此事。
姚越乃两朝老臣,年近七十,自英欢登基起便与廖峻分领左、右仆射二职,位在百官之首。
跟在英欢身边多年,知这世间女子心志亦可逼天,可却不曾想到还能遇见另一个她。
没忍住便能随便逗弄她不成?!
宫人额和_图_书上的汗层层密密,心跳趋急,再也不敢开口说话。
“出去。”贺喜转身,冷语吩咐道,目光穿过曲廊,朝内殿望去。
七月十四日,中宛黄世开部受诏退走,狄风率军疾进,连占南岵方州、蔡州、徐州、郓州、滑州、兖州等十二州,直逼南岵都城梁州。
殿中四角明烛在燃,案前灯蒙影罩,英欢一身妃红繎丝番缎罗衫,面似纸素,并未执笔伏案,身子斜靠在座背上,七分风懒三分乏,眉微挑睫低动,看他一步步走近,面上辨不出喜忧。
她眼睛睁得大大的,摒住呼吸,任他的舌在她唇上勾画,鼻间全是他身上的气息,手脚僵硬,脑中全成了浆糊。
当年新科状元郎风光无限,在朝十几年来深受君恩,只有他不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可现如今,他却一头栽在了她手上。
天色已黑,屋内犹暗,桌上一指豆大灯苗悠悠在燃。
沈无尘嘴角弯起,“只欺负你。”身子俯下来,另一只手抬起,将她散下来的发捋到耳后,温热的手掌抚过她的脸侧,“也不知你若是穿了女装,会是何样。”
一字似箭,穿心而过。
他拇指按上她的唇,眼一垂,“伶牙利齿,怎么不说话了。”
儒雅之范一瞬间全然瓦解,所剩不过是男子心骨间深存的征服之欲。
先前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狄风之部经过瘴雾大疫后仍能如此迅猛,而邺齐大军竟会在南岵境内处处受阻!
他默然片刻,额角青筋隐隐突现,低声道:“九崇殿说书、户部度支郎中,曾参商。”
趁她犹在怔愣时,他蓦地拉过她的手勾住自己的脖子,又紧紧搂住她,舌微微用力,自她微启双唇间滑进去,搅动她口中芳津,动作急切而又迅烈。
贺喜望着她,良久不发一言,目光却是越来越寒,手撩动袍摆,缓缓坐于榻边,大掌撑在软褥之上,“说。”
贺喜脚下生风,胸中腾火,人似弦弓在张,冷眸冷面一身煞气,飞快地朝宣辰殿那边行去。
英欢身子轻动,望着他,“你沈无尘好大的架子,办了趟好差便不知天高地厚了不成?”
曾参商闻言不敢再动手,生怕真的将旁人引来,只是面上更红,眼里怒火扑簌簌地往外冒,“小人!”
英欢拂袖扫案,拈指取过一封折子,垂下眼不再看他,口中道:“起来说话罢。”
英欢不再笑,心中渐明,语气凉薄道:“看上哪家的千金了?”
她受不得他这目光,兀自偏过头,“你胆子也太大了,也不先去见过皇上,便到这里来……”
小宫女执拗不已,“陛下……”
“我没有在消遣你。”他淡淡道,话中笑意消了几分。
她垂了眼,低低叹了口气,扔了笔,人伏在案前,瘪了瘪嘴,伸出手指点了点那纸上未干之墨,一咬唇,又猛地直起身子,拿过那纸便要撕碎。
英欢望他半晌,冷冷道:“将她女儿身之事公诸于世,你是想置她于死地不成?”
英俪芹嘴唇已破,死攥着被角,一字不发,满面苍容,以往鲜丽之貌全然不见。
沈无尘微笑,低头道:“陛下深思熟虑,是臣多嘴了。”
沈无尘眉微微一沉,却是不语,跪着一动不动。
贺喜目光如剑,将二人猛利地划过,而后打断道:“皇后有孕,此事确定无疑?”
二十八日,于宏、林锋楠领永兴、奉清二路禁军南下,急攻中宛淀梁,围城十日而破。
门板不知何时被人推开,甚是熟悉的声音自前方传过来,字音如雷,滚入耳中,她的手不禁一抖,任那纸又落回案上。
她是女儿身,却不似英欢那般懂得收放自己的感情,她单纯得似一纸白宣,偏又身绽奇茫让人忽视不得,直叫他想将她护起,助她成长。
“陛下恕罪。”他伏下头。
他抬眼,对上她移乎不定的目光,低声道:“倘若陛下使臣为相,臣该谏之言仍会谏,该行之责仍会行,以前怎样,以后还会怎样。”
纵是邺齐比邰涗多占了中宛三州,亦不能消祛他心中对夺不了南岵都城梁州的愤然之情!
此时西面战事缠身,军国大事悬而未决,邺齐邰涗二国缔盟未久,他又怎能轻言废后!
沈无尘闻言先是微愣,随即略显踟躇,怔迟了一会儿,才低了眼,蓦地撩袍,对着英欢重重跪下。
英欢这才抬眼,轻哂道:“若等你此时说了才调,早就迟了。京中一接到你自北戬而归的消息,便出旨至永兴奉清二路,拨调禁军南下了。”
同为贺喜心腹近侍,王如海在殿外时已同他略提过一番,此时见了贺喜他也只是行了个简礼,规规矩矩地立在内殿角落处,“陛下唤臣何事?”
这道理他自然懂,眼下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损邺齐一国之利,可他无论如何都不甘心!
他到底把她当成了什么人!
良久,才松肘拾笔,在上面勾勾涂涂,口中间或小声念叨两句。
沈无尘跪着不起,眼底有火,“陛下!”
此生头一回,比不过一个女人!
李杜二人见他入内,忙来行礼,又见他面色甚是不善,连摔殿门,不由低声道:“还请陛下体念皇后体虚、经不得这般嚣响,莫要……”
沈无尘搁在她腰间的手臂松了松,手朝下探去,轻轻一揉她的臀。
他蓦地松了手,又是咬牙,“本打算过个几年将你废了,遣回邰涗去,也算是个良局,谁知你竟自寻绝路。”他握拳离榻几步,死命压了压胸中火气,又对王如海道:“去把谢明远给朕叫来。”
虽知不可能,但他还是开口求了。
沈无尘见她不言语,兀自又道:“不论如何,陛下可依原和_图_书计,从北调兵南下,以解南岵境中邰涗军前重压。”
骨子里甚傲的他,竟也能说出这种话。
“眼下是什么时辰了?”英欢仍是慢慢道,语气波澜不兴。
贺喜负手朝内殿走去,撩帘而入,里面几个宫女俱是不敢抬眼看他,声音细若蚊吟,“陛下。”
贺喜狠攥了一把拳,改道往宣辰殿走去,步履如飞,咬牙道:“是哪个太医去诊的脉?不想要命了么?”
沈无尘摇了摇头,“北戬皇帝向晚虽是沉寡少言,未作多语,可待臣礼尚有加,北戬宰执亦有明言在前,只要邰涗不犯北戬,北戬定然不会出兵。”
就这么被他吻住,轻含慢吮,人似石僵。
“太医说,皇后有孕……”宫人不敢看他的眼,被他满身怒气吓得不轻,手脚俱抖。
宫人见他出来,慌忙上前道:“陛下,那边太医传话来了。”
贺喜眸火烧至她面上,阻了她下面要劝的话,自己抬手,猛地将那纱帐一把撩开,狠狠向下一扯,床塌之上承尘晃动一下,青纱柔柔而碎,落在地上,逶迤成团。
贺喜脸色黑得摄人,转而又看向跪在地上的小宫女,“你还是不肯说?”
从前不知她心中之苦,只怨她贪一己之情思,所以处处迫她为难她,自诩所为皆为忠臣之举,却不体察她为帝之辛酸。
沈无尘一边躲一边笑道:“……不过是篇文章而已,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贺喜声音更沉,“不愿自己说?”伸手抚过她身上的红棉锦被,其上金凤展祥,如血在泣,“英家女子,果然胆色冲天,只是你比她还要差一些。”
英欢停了停,又道:“依你之见,姚越致仕,右仆射一位当由何人来坐?”
沈无尘起身,掸袍敛袖,“谢陛下。”
贺喜盯着她,“甚好。”,走过去一点,“把衣服全脱了。”
贺喜位在上座,覆手于膝,神色沉肃,眼望前方展开的兵势图,良久不发一言。
王如海大怔,竟未想到贺喜会说出这话来,“陛下?”
曾参商一急,愤然道:“沈大人作甚么总欺负人!”
宫人点头,恭敬地禀道:“今日刚接东面捷报,皇上大喜,夜里伏案至深,一直未入内殿。”
…………
沈无尘一时哑然,心知英欢其意,不由陷了眉头。
落叶铺地,凉风骤起,又是一年秋。
她到底哪里好?竟能让他魂不守舍为之梦绕?
英欢面色稍霁,“甚好。”想了一瞬,又轻笑道:“由是看来,向晚也是个明白人。”
只是她未想到,自己从未对人说起过的这些私念,竟会被沈无尘看得一清二楚,是该喜他体察君心,还是该怨自己心藏不深?
大历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沈无尘归京;十九日,以沈无尘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位在廖峻之下;二十二日,授集贤殿大学士。
贺喜一步未留,直直前行上阶,口中冷声道:“李杜二位太医何在?”
英欢轻“嗯”一声,并不着他平身,瞥他两眼,似是随意道:“何时入城的?”
没忍住?!
可她心里却似千山相压,沉苛不堪。
“是李杜二位太医共诊的……”宫人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口中懦懦道。
贺喜皱眉,想了一下,才忆起今日一早宣辰殿那边来人,说皇后身子抱恙多日,因是特传太医前去诊脉。
他的力道一点都不大,可她却是丝毫挣脱不开,手被他箍着,腕间酥麻一片,力气俱消,不由气急败坏道:“你说的话我统统听不懂……放手!”
他停了停,笑容愈大,垂下手,转而看向她,“原来我在你心中是这般的……原先那些无耻、小人之言,是否全都不作数了?”
“进来!”贺喜话中透怒,眼仍是盯着英俪芹不移。
沈无尘看着她,眼里渐起柔意,仍是笑着道:“这不是好端端地回来了么?”又看看那墓志铭,“只是可惜了这个。”
英俪芹半枕酥锦,一张脸苍白无色,指掐掌心,望着贺喜,眼中泪光盈盈,“陛下,臣妾……”
沈无尘道:“臣启程前夜,正逢古钦一行抵赴北戬,于候馆中曾同他有过一晤之缘。言辞虽少,可隐约能辨得出来,他此次出使北戬,目的怕是同臣一样。”
宣辰殿那边早闻得圣驾将至,殿门外六个宫女早早就候着,远远看见贺喜疾步而来,忙上前躬身见驾,“陛下圣安。”
李杜皆是点头而道:“此等大事,臣等怎敢欺君,皇后已有身孕近三月,只是今日才知……”
英俪芹睁大了眼睛望着他,泪越涌越多,滚滚而落,全都滑至他的手背上,终是敌不过他掌间重力,高声泣道:“你杀了我罢!”
“臣明白。”沈无尘沉吁一口气,想了想又道:“只怕邺齐皇帝陛下亦是这般打算的。”
沈无尘眉微皱,舔了舔下唇,火辣辣的痛,挑眉去看她,见她一副怨愤的模样,不由又笑,“一时……没忍住。”
——更何况,这个女人是她。
贺喜回身冷笑,“既是这么想死,为何迟迟不自尽?”他附身而下,伸手箍住她的脖子,咬牙道:“你以为朕不想杀了你?你有孕之事一旦传至邰涗,你可知她会怎么想?”
宋沐之出列,“臣等以为,与其使朱将军硬攻北上与狄风争梁州,不若使其绕路先取南岵其余未占诸州,如是,就算梁州未取,邺齐亦可保住其余诸州之利。”
声音嘶利,一句话响彻内殿。
曾参商心底一阵悸动,怎么都没想到会听见他说这些话,言辞之间辨得出几分真情,倒叫她一时间手足无措起来,不知要如何是好……他口中所说的那个她是谁,自己心中自然是明白的https://www•hetushu•com.com,既是没法儿答他这话,也便岔开来问他道:“回来后……见过皇上了么?”
从此之后,再也无法自拔。
贺喜认出说话那人是英俪芹自邰涗带来的陪嫁宫女,满腔怒火不由更旺,冷眼将其余几人遣退后,兀自走上前去,立在榻边,沉声道:“撤帐。”
英欢浅思一阵儿,看他道:“说说。”
曾参商怔了一下,而后蓦地将手从他掌中抽出来,结巴道:“你……你该去见皇上了。”见他不动,又忙加了句:“天太晚了,我也要走了!”
先是惜她满腹才华,朝中众人能得他之所赞者屈指可数,而似她当年几取三元之事更是难得一见;后来发现她竟是女儿身,心中且惊且叹,见她在西苑林间纵马张弓射柳英姿,心又折了几分。
令她且喜且忧。
“陛下。”
沈无尘一口气念毕,蓦地笑出来,目光移至她身上,开口道:“你记得比我自己还清楚,是什么时候知道这许多事情的?”
“臣断然不是此意!”沈无尘咬牙,“陛下能否劝她弃官不做,而后臣自当……”
王如海低头道:“小臣明白了。”
英欢挑眉瞧他,面上阴晴不定,“朕何时同你说过三分天下之言?”
他负手于身后,敛去眼底之波,看了她半晌,轻道一声,“好。”
曾参商微阖之睫轻轻在颤,青涩似她,何时尝过此番滋味,浑身上下因他而软得一塌糊涂,胸前被他的身子压得微微发痛,其间又有涨痒之感,而后点点传至身上的其它地方,这感觉甚是陌生,令她又好奇又惶恐。
贺喜眼中冰茫一片,“李杜二人都是太医院的老人了,先帝在位时便特准此二人随时出入禁中,怎的现如今竟都成了老糊涂了?!”
王如海诺首而出,贺喜回身,见那小宫女倚在床塌边上,拉着英俪芹的手,哭得没个人形,口中喃喃道:“公主您这是何苦……”
曾参商火大得要命,握拳便去捶他,“还给我!”
沈无尘哑了一会儿,低声道:“臣侍君多年,陛下不必事事言明,而臣自知陛下其意……”
只是此时被英欢之言一激,才真正清醒了些。
曾参商一下子回过神来,去挡他的手时却慢了一拍,看着他已拿了那纸要读,不由急得额角骤起汗粒,大声道:“不准看!”说着就从案后绕至前面,扑着去抢他手中之纸。
夜风不凉,却吹散一头热意。
势必是要与她唇齿相合,抵死纠缠,绝不放手。
贺喜看他一眼,怒火犹盛,“护卫禁跸乃你之所责,近三个月何人到过宣辰殿来,你可知道?”
曾参商整个人被烧了个七七八八,没有一处是好的,面色溢血,眼不知该朝何处看,心在狂跳,哪里想到温文儒雅似沈无尘者,竟会如此放肆 ……
应该踢他打他,让他放开她,可人却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一般,怎生都动不了。
“说啊。”他的声音清哑淡稳。
他低眉,心中略明,声音不由低了些,“将过亥时。”
沈无尘将她手里的碎纸屑拨出,捻了袖口拭去她手心里的汗粒,又拉她近了几分,握紧她的手,“不放。”
他日夜担心着战前狄风,英欢又何尝不是?早一日调兵,狄风大胜之时便能提前一日,离京一年有余,她亦是时刻想念着他。
贺喜身子向前微倾,蓦地抬手捏过她的下巴,“说!”
贺喜抬头,见是宋沐之,不由收回手坐直,“宋卿有何想说的?”语气甚是僵冷。
曾参商面上黑红有错,恨恨地一跺脚,便要往外跑。
曾参商一低眼,想起上回在马车中他那肆意之举,不由更恼,抑住满腔愤慨之情,冷言冷语对他道:“沈大人若是想找人消遣,还请挪个地方!”
英俪芹亦是惊震不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至此他才明白,当日英欢眼中之痛代表了什么,而他那时所说之言又是多么伤人。
她下意识地一缩,望向他,见他眸间黑渊溺人,心中不禁一软,抿抿唇,便让他牵了她的手,自己不再挣扎。
小宫女在旁听得心惊,见状竟也跟着低泣出声,朝贺喜重重跪下,“陛下,皇后她身子不好,不知自己在说什么……”
贺喜嘴角微垂,狠推了一把案沿,不说话。
英欢唇角微弯,“不愧是沈无尘。”转身走回案前,笑着道:“明日便着翰林学士拟旨,除你右仆射,兼领中书侍郎;因你才列宰执,同平章事一衔暂且不加。”
沈无尘抬头,远处宫灯昏暖之光悠悠在晃,是英欢遣人来迎他了。
她推案起身,指着他,手指微颤,似是不信,“你……怎么回来了?”
此次姚越致仕,朝中老臣一派便无了靠山;廖峻在朝行事虽趋保守,可也并非不懂变通之人;由是而看,英欢长久以来所受朝中老臣们的的制肘倒可以减去不少。
英欢定了定神,再看沈无尘时面上终是露出些许笑意,“你这回差事办得甚合朕意,朝中诸臣亦赞。想要什么赏赐,但说无妨。”
她的神志于一刹那间被轰得一干二净,头阵阵发晕,眼看着他嘴角带笑,头偏侧下来,却躲不开亦发不出声……
因是不论怎样,她也不会对北戬动一指之念,只要北戬尚在,那么邺齐便不敢轻图邰涗之地。
曾参商身子一震,似被雷惊,齿间猛地一合,听他吃痛低呼,感到他松了手,这才慌慌张地使劲将他一推,自己朝后退了两步,脚下软似棉絮,被他碰过的地方如火在焚,开口时声音也不似平日里自己的,“你……你怎能……”
紫毫饱蘸浓墨,挥笔其上,洋洋洒洒数百字,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