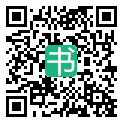第69章 乱草昏鸦,连鬟并暖处
唐天霄低低地呻|吟一声,丢开灯笼将她拥到怀里,紧得像要把她揉到自己骨血里,再也不能分开。
“这……”
刑跃文应诺时,唐天霄已站起身,拂袖向外走去。
刑跃文一愕,道:“陈参将是定北王的心腹爱将之一,戍守边疆已有八年不曾回京。此次因母亲大寿,边疆暂无战事,才告假回京探亲。贵妃娘娘莫非有何疑问?”
宇文贵妃不理会他,站起身向唐天霄说道:“皇上,既然连证人都真假莫辩,不如且把此案押后,待证人身份清楚了再说吧!”
唐天霄差点从干草上跳起来,讶异道:“你说什么?”
看着刑跃文时,是刻骨的恨毒;
她不孤单,他也不孤单。
“你想告诉我时,自然会告诉我。我只要知道你的确已经不想取我脑袋了就行。”
“你便是可淑妃?”
突尔察再望向她一眼,忽然一侧身,在众人的惊呼声中,狠狠撞向了坚硬的墙壁。
两人都没有说话,呼吸却同样的不均匀,彼此胸膛内的汹涌和鼻息间的哽阻在静夜的空气里也同样的清晰。
可浅媚感觉着他的忐忑,展眉一笑,“唐天重的确想杀你,不过清妩姐姐讨厌血腥,只盼着岁月静好,一世安然。我在花琉半年,本来的确是想和她学些宫中生存之道,她倒是事事都愿意和我说,可惜一有机会就劝我趁着和亲之机化干戈为玉帛。她说若得两国太平,再无杀戮,既是天下的福分,也是我和她的福分。她又说你年少多才,潇洒不羁,可惜错生于帝王之家,否则便是我仗剑天涯笑傲江湖的绝佳伴侣。”
皇帝发了话,这审讯自是进行不下去了。
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并不是某个人的权力,而是某个阶层的权力。
唐天霄今年已经二十有四,大婚多年,妃嫔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偏只有个下等宫人生下一个资质平平的皇长子,并不为宣太后和周帝所喜。众人只从宇文贵妃的受封和受宠,便无人不知当今皇室对皇嗣的看重。
可浅媚奇怪地望着他,“你怎不问我,为什么后来改变了主意?”
可淑妃长得很像当年的宁淑妃,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
“得了,丫头,别哄我了!宁清妩连我和她一起时让我睡软榻都和你说了,不把这些事告诉你才怪!”
他搂着她的怀抱温暖柔软,神情却豪宕昂扬,仿若矫龙出海,旭日破空,锋锐如刀刃初发于硎。
可浅媚疼得紧紧蹙眉,也已说不出话来,却再不肯放弃好容易抢到的有利体|位。
可浅媚又问唐天霄:“你也说过喜欢我,那且请大周皇帝陛下告诉我,你又喜欢我什么?”
她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纤瘦的身影埋入了深沉的黑色里,仿佛与陈旧的墙壁融作一处。
男子并未往后看,发现干草堆里没有人,才提高了灯笼,惊诧低唤:“浅媚!”
三寸长的钢针,扎入了她的指甲缝间,然后施刑人捻起圆柄,一点一点不紧不慢地往里旋着……
待他退出去,唐天霄低头瞧瞧可浅媚沉睡的憨态,小心地扶了她一起躺到披风和干草临时铺就的褥垫上时,却觉她蹙眉往他身畔靠了靠,却是枕了他的胳膊,钻向他怀里的姿态。
可浅媚难得那般安静,乖觉地靠在他的怀里默默地听他揭开自己的小伎俩,红着面颊一言不发。
外面守候的卓锐久久听不到动静,轻轻推开门查看。唐天霄摇摇头,示意他在外守着。
“必要之时,我会弹压。母亲也只是怕我一时顾虑不到,这才代我出手,真若有事,她不会介意处理掉任何挡我跟前的人。”
但他的脚步并未稍作停留,甚至没有看她一眼。
唐天霄狼狈,旋即道:“我只怕她说了我不好的话,你便都信了。”
这是自唐天霄到来之后她第一次直接和他说话。
喉间没来由地微哽。
什么时候大理寺的监狱里待遇这么好了,受了刑的犯人能给上药包扎?
从小窗往外看去,唯见老树荒草昏鸦,是连夕阳余辉也照不到的角落。
刑跃文呆坐在主位,盯着倒地的可浅媚,便是准备了千条万条置人死地的罪名,也已作声不得了。
突尔察如困兽般开始就一直嚎叫着的,嗓子也已嘶哑得不堪,只是被几人奋力压紧在青砖墙上,再也不得动弹。
“闭嘴!”
入夜了。
“嗯,我是欺负你了。不过,那不是如你所愿吗?”
密室中一时静寂。突尔察早已没了呼吸,热血却还在汩汩冒出,空气里弥漫的新鲜温热的血腥气令人憋闷得透不过气。
握了她纤长的腿,他待要奔往正题时,她却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灵活地一翻身扑到他身上。
那人声,竟意外地有几分耳熟。
卓锐犹豫片刻,把自己的披风也解了,铺到干草上,轻声道:“让淑妃卧下睡,更舒服些。”
这一招,算是釜底抽薪之计了。
“笑……笑话!我怎么知道你和庄碧岚有什么渊源?”
然后,厚重的铁门扇被推开,身后破落的墙壁随之嗡嗡震动着,像成群的小虫子在背脊爬过,让皮肤麻麻的。
幸福……
他扎手扎脚地仰面倒在地上,怒目圆睁,大汪稠厚的鲜血在他头部汩汩溢出,慢慢在地面上汪洋开来。
“可惜,这位故人,四年多前便不在了。”
手碰到唐天霄的面庞时,指上的疼痛让她“哎呀”一声叫出声来,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你倒与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唐天霄便无语。
又是一句废话了。
“我让人打你耳光把你打成猪头了?”
唐天霄不觉听得痴了,“她……她真的这么说?”
不晓得有没有被这些人将指骨夹裂。
庄碧岚倒也寻常,身兼兵部侍郎和骠骑将军,都算是闲职,上衙门做事不过应个卯,并不管事。
“突尔察!”
唐天霄却已失态,竟身体一晃,跌坐回椅子上,铁青的脸色已转作苍白,看向可浅媚的眼神极是古怪,竟抿紧薄唇一言不发。
含恨之时,她下手自是不会容情。
宇文贵妃紧随他离去,待跨过门槛,只听她低低道:“皇上,把手上的伤包扎下吧https://m.hetushu.com.com!”
在谁的身上,她曾看到过这样指点江山的非凡气势?
唐天霄微笑,却又禁不住有些失落,“你肯依顺我,有时还刻意讨我欢心,便是为了赢我宠爱,以求两国和睦?”
“是,《薄媚》是由同一宫调的十支曲子组成的大曲,可歌,可舞,可弹奏,讲的是越王用美人西子施展美人计复仇之事。吴灭越兴,西子被目以妖类,殒于鲛绡之下。”
他目光悠远起来,神情是从未见到过的复杂异样,仿佛揉着说不清的向往、钦敬和憎恶。
可浅媚便笑得诡秘了,“其实我也猜到你是在试探我。所以我就故意让人射了一袖箭。”
唐天祺笑道:“部里转来的案卷里已经载明,咱们不用多说,请刑大人抓紧时间问案吧!”
干草给略一翻动,便能看出上面粘连的污物,也不知上一任在这里呆过多久,说不准是血流得光了,给人横着抬去了乱葬岗。
可他有个了不起的父亲是驻守西南重镇的交王庄遥,他还有个了不起的红颜知己南雅意让唐天霄多少年放不开,他还有个了不起的亦敌亦友的主上叫唐天霄,不愿让他好过却不肯让他受委屈……
侧部倒也有个小窗,即便比拳头大不了多少,也用数根拇指粗的铁栅浇铸于墙中。
一低头,她靠在他肩头,垂着眼睫,竟然睡着了。
“她极公允,没说你甚么坏话,也没说她夫婿甚么好话,甚至也说我愚蠢,放着自己快活小日子不过,卷到男人你争我夺的腌臜名利场里,也是个笨女人。她还教了我一支大曲,叫《薄媚》,其实便是想我远离这些家国是非。”
“让她扎吧!”
败也龙嗣,成也龙嗣。
许多种感情的交集,也许有的人听不出,但和她山盟海誓过的人,会听不出吗?
如今,只剩了沈家和那些附和的朝臣,可浅媚相信唐天霄应付起来必定游刃有余。
唐天霄振奋了些,“还为什么?”
唐天霄是说了让礼部和兵部派员参审,可也犯不着派这两位只在两部挂着闲职的大员过来吧?
他下意识地便要闪避,可身躯微微一动,又站定了。
可浅媚“噗”的一笑,又道:“其实你也未必便怎么俊美。我瞧着庄大哥容貌便比你端正些,那等温雅清贵的气质,更是胜你十倍。便是天祺,也似比你年轻可爱些。”
唐天霄自幼通读史书,却也晓得这故事,点头道,“哦……史载,西子心仪的似乎是吴国的一位大臣,可在越十年,却爱上了越王。越王自尽,不论是和谁,西子都已回不去了……”
以刑跃文的官阶,便是派了礼部侍郎或兵部侍郎来,多半也只有听审的份儿;
“哦!”
也许,只是在不经意攥紧梳子的时候。
等那边有人通报说礼部任职的成安侯唐天祺和兵部任职的交王世子庄碧岚奉旨过来参审时,他更是皱眉。
小窗的一点微光渐渐也消失了,鸦啼声也渐渐零落。
她只作不认识,正要问他姓名时,忽然重重地打了个喷嚏。
“我的天哪,你也忒胆大,还从来没有女人敢……”
指上所施的刑罚虽不致伤及性命,到底备受痛楚,半日折磨下来,想来也倦乏得厉害了。
怕碰着她受伤的手,唐天霄一晚上不敢动弹,睡得极浅,待她一动,即刻清醒,微笑问道:“可觉得好点儿了?”
刑跃文张口结舌:“这个……这个……微臣一心想铲除邪佞,以清君侧……”
刑跃文又道:“好在我们经过彻夜盘查核对,又找出两位证人来,可证实可淑妃故意把北赫随从留在宫外撇清自己,不过是暗渡陈仓的把戏。她有当年南楚信王留在宫中的余孽作内应,又何必再要那些招人眼目的北赫人帮忙?”
她恍惚哆嗦了一下,蓦地睁眼,才觉出十指突突的疼痛。
“既然你是冤枉的,便不该胡乱招承。再加上随口攀污朝中要臣,闹得大了,光查案就可以查个一年半载,我想护你一时也护不下来。你想在这牢里过年呢?”
白得鲜艳的衣衫带出一阵风拂到她的面颊,有点冷。
可浅媚待要不理他,他却只是陪着笑脸,取了钥匙先把她手脚上重达数十斤的镣铐去掉,小心扶她在铺了披风的干草上倚在自己身畔坐了,又取了梳子出来,一下一下地为她梳凌乱的发,并把发间纠结的污物一点点拨去。
可浅媚并没有问唐天霄下一步会怎么样。
“其实我宁愿你快活着,一直这么快活着……”
他的目的,就是要她看看她的母族对皇权和他这个皇帝的挑衅。
众人都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未及回过神,竟然拉她不住,由她冲到突尔察跟前,呆呆地望着他,然后颤着嘴唇,凶悍地瞪向刑跃文,然后是唐天霄。
若真的骨头裂了,以后若再舞鞭或耍剑,还能那般利索吗?
“还有呢?”
这一觉可浅媚睡得很香甜。
跟着宇文贵妃的两个侍女胆子小些,不敢看可浅媚受刑,其中一人偶尔瞥向突尔察,忽然发出一声惊叫。
宇文贵妃冷叱道,“什么清君侧?古来想清君侧的大臣,就不曾有过一个对皇帝或皇权存有敬畏之心!景帝时的七王之乱,就打着诛晁相、清君侧的口号,可景帝斩了晁相,可曾阻住七王叛军攻往京城的步伐?燕高宗也曾清君侧,却是连他侄儿建文帝给一起清了,自己当了皇帝!你们想清君侧,到底是何居心?”
若是旁人,见这万万人之上的帝王陪自己在牢中窝了一整夜,不晓得该多感激。可浅媚却摇头道:“睡得不舒服。你的胳膊忒硬,硌得慌。”
唐天霄也不着恼,微笑道:“你既无害我之心,我若倾心待你,只要你心里并无他人,总有一日也会倾心待我。只是昨日审案之时听你提甚‘公鸡皇后’,又说我‘高高在上,独一无二,谁堪匹配’等语,我心里便难受得紧。当年我年少气盛,备受摄政王父子凌逼,因形势所迫不得不纳了沈氏等人,虽是虚与委蛇,却着实不快。我从不与旁人提及这些心事,却把清妩视为和-图-书红颜知己,也曾多少次向她嘲笑沈氏形貌如公鸡,见之生厌。但她终为唐天重和我反目,咒我将一世孤单……”
“没……没有了……”
虽然忌惮沈家,但若不是沈家突然和定北王部属联手,即便真给打个措手不及,也不至给逼到眼睁睁看着心爱妃嫔被人用刑还袖手旁观的地步。
她的身体忽然剧烈的颤栗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再次被带到密室时,可浅媚看到刑跃文那张黑髯长脸,想起惨死的突尔察和自己所受苦楚,已是恨怒皱眉;
或许是睡着,或许不曾睡着,模糊间,又见芳草碧于天,黄衫飞白马,欢快的蹄声和笑语直冲云霄。
“天下虽大,人的心更大。再大的天下,填不满一颗人心。是非成败又怎样?何必为根本无法餍足的欲望计较太多?浅媚,这曲《薄媚》,我劝你不必弹了。”
“对不起。”
她的声音已经惨叫到嘶哑,却字字清晰凌厉;凝望向他的眸子在红肿脏污的脸上更显得乌黑动人,却是水气迷蒙。
可浅媚不依不饶,滑溜溜的小小舌尖便往他唇舌间扫,待他回应,却不轻不重地咬上一口,冷笑道:“我欺负你了?”
唐天霄吐一口气,向她微笑:“那个……我认罪。荆山顶上那场谋刺,是我安排的。我遇刺时,你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和刺客联手杀我。”
唐天霄冷笑:“生?她们生得出吗?”
“于是,你堂堂一国之君,便由着他们欺君擅权,作威作福?”
看到那人背影,可浅媚忽然间耸紧了肩,抿紧了唇。
这时,一直沉默着的宇文贵妃忽然扬声问道:“刑大人,这位陈参将,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许久,但听轻微的“丁”的一声,她阖在双掌间的钢针掉落在地。
密室里顿时也是一片惊呼,如果可浅媚有气力张开嘴巴,多半也会惊呼出声。
唐天霄叹息道:“你们都当我是傻子了?人人都说我鸠死康侯,清妩殉情,连太后也这般哄我,我便装了回糊涂。我从来都不想伤了清妩,便是康侯么……”
宇文贵妃轻笑道:“我自是有疑问。陈参将的确是我父亲军中的,我自小便见过。此人长得倒是和陈参将有几分相象,只是个子矮胖多了,眉眼也有差别。陈参将回京探亲不假,可多半在路上被长得相象的歹人看到了,所以在路上截杀,夺了公文冒充他回京行骗吧?”
“谁想弄死你了?”
棕黄色的梳子和大团殷红一闪而逝。
宇文贵妃也是聪明人,她当然明白,他是在告诉她,他对爱妃受人诬陷之事心中已洞如烛火;
衣襟散落时,又见她脖颈上那点鲜红如珊瑚珠般的痣。
低而窄,阴暗而潮湿。
可浅媚依旧抿着唇瞪他,黑眸却已一片氤氲。
可浅媚抽气,却笑道:“天霄,这是胎痣,投多少次胎都还会长在原处。若是今日用刑重,不小心把我弄死了,等个十六年,你可以凭这胎痣再找到我……唔……”
在灰暗霉腐的牢房里,听一位帝王表白他的雄心壮志,实在有点诡异。
可浅媚不以为然道:“我们就那么几个人去的,行踪够隐蔽了。我并没请杀手;成安侯是你弟弟,自然也不会害你;庄大哥么,我晓得他和你一直有心结未解,可雅意姐姐还在城里,他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敢谋害你拖累了她。跟你们的从人更不用说,个个都快成了只知道听主人话的偶人了,哪会打这些主意?何况你当时还没怎么把我放在心上,特特带了我出门本就奇了,给刺客袭击时居然还敢腾出手来救我,明明空门大开那些刺客居然打不着你……我见了就气,所以无论如何要打死你手边两个高手,让你这般的无耻!”
“你不孤单。”
刑跃文一眼看到她包扎着的手指也是皱眉。
可浅媚被送到了大理寺的牢狱中,并且是牢狱最深处被单独分割开的一间。
一个宫廷禁卫服色的男子缓缓踏入,提了一盏标着“大理寺”字样的普通灯笼,小心翼翼地查看着。
醒来时她甚至和平时在自己房中睡醒一般,舒展着四肢伸了个懒腰。
唐天霄垂头将那丝帕解了,随手掷到一边,把灯笼在墙缝中插了,才解了披风铺到草上,笑着问她:“是不是嫌脏了睡不下来?且忍一忍,先过来坐坐罢。地上毕竟冷,小心着了凉。”
她对中原的发饰原就不甚了了,好容易学会的几种也不熟练,唐天霄看她梳妆能看会一两种,于他这种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皇家贵胄,也算不容易了。
她垂着眸,虽不痛楚呻|吟,但每根针带着一溜鲜血拔出时,她的身体都会因疼痛颤动,鼻翼满是汗珠。
话未了,镣铐声响过,背后风生忽起,忙转头时,但见可浅媚用双掌夹着一枚钢针,劈头向他刺去。
他们曾在荆山相处过,离得近时,偶尔的确能闻着他身上有极清极淡的某种气息,却连香气也说不上,又怎会突然携带这等浓郁的芳香。
贵妃出面亲口否认了陈参将的身份,等于否认了宇文家和这件事的关系,京城便有再多定北王的亲信或部属,都不方便再搅到这事里了。
因是密审,他并未着官袍,依然是一袭式样简约的大袖素衣,翩飘蕴藉,衬得他容颜如玉,风仪出众。
密室中并无女人,唐天祺便上前,亲自抱了“晕倒”的可浅媚就近送往干净卧房时,可浅媚算是想明白了。
可浅媚笑了起来,本来就肿着的眼睛笑得只剩下弯弯的缝儿,“倒也不全是。”
众人一怔,顺着她眼光看时,他未流泪,却是目眦尽裂,竟然慢慢地滚下两滴鲜血。
他仿若是不以为意的自嘲,唇角笑意散淡不羁,可握住的掌心却渗着汗,暖暖地湿润着她的手腕。
唐天霄的神情也暧昧起来。
可浅媚眼神有些飘忽。
唐天霄并不意外,叹道:“没错,北赫和大周几十年的死对头,李太后的家国又被大周给灭了,她送来的公主,没一点自己的盘算才是怪事。”
见唐天霄也望向他,突尔察忽然不挣扎了,他站定了,用很慢https://m.hetushu.com.com的语速,说了好几句话。
“母后让我前来和亲,的确想叫我迷惑于你,伺机让大周内乱,以便他们就中取利。可我被送到花琉和清妩姐姐住了半年,听她文绉绉讲了许多话,也便渐渐改变了主意。我想,如果我赢得周帝宠爱,两边劝和,说不准便能如当日出塞和亲的明妃一样换得边疆百年安宁,不论是母后,还是……还是北赫的好友们,都不用再担心未来血流成河,朝不保夕,岂不更好?”
他慢慢说道:“其实若非他苦苦相逼,我也不是非要取他性命不可。如今他远在花琉,真能这般和平相处下去,也算是一桩好事。但他恨我入骨,必与相距不远的北赫国同仇敌忾。北赫欲遣个别有居心的公主前来和亲,先派到他那里取取经也是正常。”
可浅媚大度地拍了拍他的肩,说道:“你这人什么都一般般,根本不如清妩姐姐说的那般好。不过还算有几分美色,本公主甚是喜欢。”
他将会为她重新支起一片天空。
猜着他多半没什么好话,可唐天霄还是铁青着脸追问。
她的眼底虽满是泪水,却似有烈烈火苗在突突跳动。
他亲住,双手却抚向那兀起的峰峦,直攀峰顶……
这次是他理亏,斗嘴再斗不过她,但另一方面的能耐却胜她十倍不止,轻而易举便让她在他臂腕间绷紧身体红涨了脸。
唐天霄也正望着她,冷沉的面孔上没有一点表情,连脊背都似僵硬,偶人般沉默地坐着,再不答话。
狠狠一针,扎入他的肩膀,然后是第二针,第三针……
“《薄媚》?”
悲切,愤怒,失望,不屑……
刑跃文惊得忙喝道:“大胆!你敢对皇上出言不逊!”
他低了头,神情颇是无奈,眼眸却是清亮含笑,并无怪责之意。
唐天霄瞪她半晌才道:“你这丫头没规没矩,胆大妄为,连大周皇帝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都抢着给说了做了,还想着蛊惑君心,算来只有缺点,没有优点。不过也还算有几分美色,本公子甚是喜欢。”
“没错,请问,你是……啊嚏!”
“欺……欺负?”
可浅媚疼得在地上翻滚着,挣扎着,哑了的声线终于不再尖锐,大刀斫过树皮般闷闷的,却已转作了痛不可耐的沙哑痛哭。
那样的重刑之下,她虽是凄厉惨叫,可始终未落一滴眼泪。
“还不无耻吗?你明明已在怀疑我,只怕试探出我有什么不对了,立刻便会将我处死,可居然还在前一晚欺负了我!”
他也不嫌她脸上脏污,又将她面颊亲了一亲,低低道:“好罢,我承认你赢了。我未始没想过你可能另有居心,第一次欺负你时,的确也只是想欺负欺负你。后来却不小心落你彀中,见你受了伤,总觉得亏欠你,只怕你有事,便时时记挂着,不知怎的……便记挂出习惯来了!”
可浅媚身体有些僵硬,忽然一阖牙关,向他咬落。
是香气?
可浅媚难得这么中气不足:“你怎么晓得我认识清妩姐姐?”
“何况宇文启已经老了,后继无人;沈度爪牙虽利,可惜刚武有余,谋略不足,他儿子沈朝旭,更不比我那脓包皇后强多少。我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等到他们的衰败和衰落,——然后,一击必中!”
唐天霄面色略略缓和,点头道:“便依贵妃所言。既涉及两国邦交和相关将士,可令礼部和兵部派员协查。”
庄碧岚站在她跟前,说的却只是些闲话:“下官庄碧岚,奉旨陪审此案。”
唐天霄吃吃笑着叫骂。
钢针虽细,刺得却不浅。
“我……我怎的就无耻了?”
她道:“你没用。你不配。”
这一回,他的袖子拂到了她的鼻尖,却没有了那种浓郁刺鼻的香气了。
唐天霄无语凝噎。
三个太医都说可浅媚怀孕,成安侯和庄王世子也力证可浅媚怀孕,所以可浅媚就是怀孕了。
挑衅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她会被牵累,至少也会让唐天霄猜忌嫌弃。
她留意到他掌心一排深深的梳齿印迹,犹有血水渗出;而肩上被她用钢针所刺之处,虽是深色衣衫一时看不大出,却也觉得出衣衫已湿了一片。
可浅媚呆呆地望着他,忽然叫着他的名字,左右肘连着出击,硬生生撞开有点懵的行刑者,飞快地扑向突尔察,其中三根手指上,犹自钉着颤巍巍的钢针。
她嘀咕道:“我不要在下面,脏脏的,说不准有什么虱子跳蚤之类的……”
他的唇角没有素日的慵懒散漫,抿着向上的弧度刚毅果决。
“你故意和庄碧岚亲近,不就是为了引我注意?你明晓得我再也无法容忍庄碧岚觊觎我的女人!”
她用手背碰了碰墙边凌乱铺着的干草,却也是潮潮的,一只小老鼠被惊动,不紧不慢地沿着墙边踱到墙角,再往里一钻,并看不出有多大的缝隙,却噗溜便不见了。
卓锐迟疑着,许久才道:“他说,公主不该信他人摆布,嫁到中原来。”
刑跃文大惊,忙跪下连连磕头,“微臣不敢,微臣不敢!”
可浅媚背上猛地冒起冷汗,腰足本就已万分绵软无力,此刻再也支持不住,一晃身栽倒在地。
正疑心着自己是不是幻听时,有锁匙转动碰撞的声响清晰传来。
可浅媚盯着他俊朗的面庞,忽然感觉唐天霄这样的气概似曾相识。
而站在最顶端的那个人拥有着颠倒黑白的最高权力。
但唐天霄亲自踩向她的手时,她哭得像个孩子;
她像一尊美丽的雕塑静静地立在灯影之下,黑发离披,黑眸冷锐地盯着唐天霄,虽是面庞红肿脏污,却丝毫不觉丑陋。
她自到了瑞都,所到之处无不蘼丽繁华,连偶经市集,亦见满街珠翠,绣衣金缕,处处歌舞升平。
唐天霄叹气,“我只是给打了个措手不及而已!都预备好了去接你了,那厢忽然闻报,沈度跑太后那里告了一记黑状。待要去周旋时,太后懿旨已下,我只来得及让卓锐和陈材赶过来先照应着。若那些人有意取你性命,或施用可能取你性命的刑罚,他们必会拿了我的手谕出面阻止。但不到那个地步时和图书,我并不想弄僵。”
——经了一夜的准备,即便没有了宇文家为同盟,置她于死地的“铁证”应该更多了吧?
唐天霄平日里的性情极好,又着实心怀歉疚,见状也只是啧啧嘴,并不和她计较。
谁也不曾想到,看起来事事漫不经心的唐天霄,竟有如此记忆力,竟把突尔察方才所述之话硬是一个音节也不落下地复述下来,尽管他根本不明白那每一个音节都代表着什么意思。
他批了她一圈儿,却还是不敢以皇帝的势派来压她,末了只以“本公子”自称,却是低了心气刻意讨好她了。
不过她好像忘了,有利的体|位也未必就代表能占据上风,忍受不了痛楚呻|吟的似乎还是她……
她想摸下他梳的髻到底是怎样的形状,指尖才触发丝,便已疼得哆嗦。
“说!”
“让你再嘴不饶人!”
她留意到他手边缠着块丝帕,质料极好,边角处绣了朵小小的青梅,便道:“她帮你包的?既然领了人家的情,何不日日夜夜陪着她去?”
正在酷刑下煎熬的可浅媚恍惚听到两句,蓦地转过头,睁大眼盯向他,已满是惊恐。
他咬牙站着,由她刺着,连哼都不曾哼一声。
“如我所愿?”
他低声向可浅媚说着,嗓子喑哑,压在喉咙口般沉闷着,“我没用,我不配,我辜负了你。”
唐天霄仰头,幽远的目光似透过了垢迹斑斑的屋顶投往渺杳的苍穹深处。
唐天霄吃痛,却又不舍得将她放开,静默着只与她缱绻。
太医院三位最有名的太医很快奉命前来,口径出奇的一致:“皇上大喜,淑妃娘娘已有身孕二月……只是淑妃娘娘受惊过度,身体虚乏,需长期静养……”
唐天霄摇头道:“不是这句。是他后来向朕说的话。”
话音落下,他才觉出失言,忙要找话解释时,耳边已传来细细的酣声。
他也不说话,将她手指握住,一根一根含到口中,轻轻吮去污血,吐到一边,然后涂了药,为她一一包扎好。
他小心地把她的伤手挪到不易碰到的位置,将她抱得更紧些,一动不动地坐着,由她沉睡。
若可浅媚怀了皇嗣,便是有天大的罪名也得搁在一旁,先让她安稳生下皇子或皇女再说。
打了个呵欠,她懒懒道:“你就慢慢吹吧!等那只公鸡下了蛋或者你的容容生了小天霄,你的天下还是有一半属于他们!”
待得说完,两人都怔住。
这时可浅媚忽道:“可烛公主是北赫最美丽最耀眼的雪莲花,多少少年儿郎竞相追逐。他们个个英勇,愿意不惜性命守护公主。”
外面有人低声惊呼,一道人影窜入,将可浅媚臂膀捏住,却是卓锐。
刑跃文知这二位都有点脾气,也不敢托大,笑着解释道:“昨日有位陈参将,本来力证这个可淑妃并不是真正的可烛公主,但一早因为定北王军令急召,已经离开了瑞都。”
可浅媚哂笑,眸光淡淡流转,“刑大人多心了!我不过是转述突尔察的遗言罢了,又岂敢对皇上大不敬呢?皇上高高在上,独一无二,谁堪匹配?这一生一世,也只有公鸡皇后之流有那个福分长长久久侍奉着罢!”
有女子微笑,眸如春风,搅动一池春|水漾漾如歌。
他们自是装作不认识。唐天祺负了手昂首阔步径直到侧面的一张案几前坐了,并不看她一眼;而庄碧岚却在走到她跟前时顿住了,站定身体打量她。
终于开口,先倒是这等拈酸吃醋的话,连可浅媚自己都惊讶了,忙冷了脸,别过头去再不作声。
唐天霄瞧见,眼眸便晶亮了些,侧头亲亲她的唇,然后滑入她口中,追寻她的柔软。
可浅媚恨恨地又咬他,又问:“我让人用夹棍夹你了?”
他问她:“清妩和唐天重向你说了我多少坏话?我这么个十恶不赦的男子……若你不是真心相待,每日笑脸相迎,大约也吃力得紧罢?”
可惜他还不知道唐天祺、庄碧岚和可浅媚的渊源,否则倒是可以要求这二人回避另行择人了。
但他既然敢和她缠绵到天亮才离开,无论如何应该已经有所安排才对。
她忙笑笑,把凝噎声吞下,轻轻吹她辣疼着的手指。
只听庄碧岚惊呼一声,凝神又搭上她另一只手腕,然后失声道:“淑妃……似乎怀孕了!”
重重的“咚”的一声,将可浅媚的惨叫硬生生堵了回去,连手上的剧痛都觉不出了。
唐天霄哼了一声,忽然发出一长串北赫音节,然后说道:“还有这些,你没全译完吧?”
哪怕他们都是第一次睡在这样肮脏阴暗飘着死亡气息的牢狱之中。
“我并不怕他们,我只怕闹得大了,又兴刀灾。中原诸国并存达六十年之久,其间战争不断,不知多少百姓流离失所。五年前大周终能一统,却又来了场康侯之乱,连一向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都是人口骤减,仓廪空虚,更别说大河南北,天灾人祸不断,久已民不聊生。四年来,我专心吏治,疏通河运,鼓励农桑,尽力与民休息,好容易有点起色,实在不愿意将这些成果毁于一旦。”
“咦,你很在意她怎么说?”
不过,可浅媚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她又曾多少次为之心折,以为那就是英雄?
唐天祺身为皇室近支,自是最为激动,忽然便站起身,高叫道:“快,快,快去传太医!这还了得,这是龙嗣,龙嗣呀!”
他疼得身体颤了下,终于松开她,凝视她半晌,伸手为她拭去眼角的泪。
庄碧岚首先反应过来,抢过去便搭上她的脉门。
“皇上!”
庄碧岚拈着茶盏,却不喝茶,淡淡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却是连半句废话也不说了。
给连着轻咬了几口,唐天霄不晓得她这算是挑衅还是挑逗,舌尖没觉得怎的疼痛,倒觉得别处给蹭出了腾腾的火焰,烧得难受。
陈参将唬得忙跪下磕头道:“贵妃娘娘,末将的确是陈参将。贵妃入宫之前去静安寺上香求平安,还是末将护送的呀!”
那亲昵的温暖包围住伤痕累累的手指时,她又要落泪,连忙忍了,愤愤道:“既然想把我活活弄死,现在又何必惺惺作态?hetushu.com.com”
经过可浅媚时,她正将自己指尖上悠悠颤动的钢针举高,用牙齿咬紧末端的圆木柄,将深入骨肉的针一根根拔出。
她是吃尽苦头,他看着也是备受折磨,而宇文贵妃何尝不是如坐针毡?
所以,即便可浅媚有害她落胎的嫌疑,即便可浅媚的到来已分去了帝王一大半的宠爱,她不得不选择唐天霄为她预备好的那条路。
是他袖中传出的浓烈的香气?
唐天霄极不适应有人用这样近乎鄙视的眼光看着自己,不觉避开她的目光,问向卓锐:“刚才,突尔察在说什么?”
可浅媚眨巴着眼睛望着壁上还有一星光亮的灯笼,忽道:“其实我本来真打算摘了你脑袋或盗了大周兵防图的。”
“我用钢针扎你手指了?”
待得收拾齐整,他自己端详了一回,大约觉得不甚好看,有点尴尬地咳了一声,道:“可惜我只会绾这个髻,还是看你梳了几回才记得的。”
好在可浅媚习武之人,身体底子甚好,手指虽然还是有些疼痛,到底上药处理过,却不曾发烧,熟睡了一晚精神也恢复了不少,躺到唐天霄的胳肢窝下还有力气又往中间挤了挤,自己霸住了那件披风铺着的干净地盘,却把唐天霄挤到脏污的干草上去了。
昨日他带宇文贵妃前来听审自是别有用心。
不过,她还有机会再握住被唐天霄亲自解走的鞭子吗?
牢中自是没有镜子。
更妙的是他居然记得带了根不惹眼的素银簪子进来,把拢整齐的发在脑后绾了个简单的髻。
但不可否认,这种气势让她觉得很踏实,好像只需沉睡到这人臂腕中,便是天塌下来也无需担忧。
庄碧岚又道:“淑妃和下官当年的一位故人,长得颇有几分相像。”
乔装而来的唐天霄依旧提着灯笼,眸光清寂黯沉,如此刻窗外浓得化不开的夜。
“你是君,他们是臣。难道那位沈大将军比当日的摄政王和康侯还厉害,所以你怕了?”
有男子叹息,声音和他的目光一样,苍凉而温厚。
可浅媚一听是这两人来了,便猜想今天自己应该不用太遭罪了,却想不出他们会用什么法子来应对为她罗织的罪名。
可唐天祺不但是封了侯的皇帝堂弟,更是手掌京畿八万重兵的年轻将帅,跺跺脚瑞都城晃三晃的主儿;
他惋惜地叹气,再抛完一句废话,终于走到另一侧的案几前坐下。
刑跃文待二人都坐定了,笑道:“侯爷,世子,相关案情,大约都知晓了吧?”
那飘动的细碎清纹,据说叫幸福。
卓锐正惋惜地看向突尔察,闻言脸上浮过一丝犹豫,才答道:“他一直在喊他们的公主冤枉。”
不致十指连心般疼痛,却也够呛了。
卓锐放开了捏住可浅媚胳膊的手,垂下头慢慢往外退去,轻轻关上门扇。
谁也不晓得,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晓得,他是什么时候被梳齿扎伤了手。
“哪怕你明知我是冤枉的?”
他抚着可浅媚的面庞,微笑道:“你心里也清楚罢?其实……你长得和清妩着实有几分相像。若再与清妩一般的贞柔婉顺多才多艺,我必定起疑,所以你一到瑞都,便故意显得卤莽无礼,了无心机,还装着不识字逗我,以释我疑心。可你必是晓得我与清妩并无夫妻之实,向来她睡床上我睡软榻,所以第一次便推搪我,要我到软榻上睡;只清妩知道我其实甚是寂寞,才每每沉溺歌舞,并爱出宫游玩散心,所以你便每日陪我练剑跳舞,弹琴说笑,让我想闷也闷不起来。——便是我们初在一起,你欲截我头发结作一处,也该是晓得我其实满心盼着有个真心待我的女子出现,刻意想以此让我另眼相待罢?你又不是那种养在深闺没见识过好男儿的大家小姐,没道理这么快便对我情根深种。”
可浅媚连忙转头时,只是唐天霄正飞快将右手藏到袖子中。
而原来的那个人……到底遥远了。
卓锐变了脸色,不敢说话。
她小产不久,根本不宜见风,却在这时候被带出来看这种血腥之事,与其说是宠爱,不如说是警告。
外面有急促的脚步声和低低的人语声。
攥得越紧,伤得越深。
可浅媚更是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已经不想取你脑袋了?”
现在她亲口责他不肯相护时,她又是抿紧唇泪光点点。
昏暗的灯光下,他微微的笑容月辉般明洁。
刑跃文明知她语带嘲讽,话里有话,到底不明因由,再不敢接话头了,只是拿眼觑向唐天霄。
宇文贵妃眉目不动,淡淡道:“可又胡说了。我身体不大好,可记性还算不错。我怎么就不记得定北王府附近有什么静安寺?陈参将八年不曾回京,人事早非,只怕连他亲生母亲都分不出真伪了吧?刑大人也太过大意了,找来的证人,怎不细细查问背景,找了个假冒之人过来?”
“我是怕了。”
他呻|吟一声,伸手便松她衣带。
她不敢睡上去,拖着沉重的镣铐一步步挪到靠近门边的角落,用鞋底胡乱把地面蹭了蹭,才疲倦地靠墙坐了,将满是伤痕的手搁在膝上,把头靠在胳膊上养神。
但对着唐天霄时,更多却似轻蔑和不屑。
唐天霄惊得站起身时,突尔察已经无声无息地顺着墙壁滑落下来。
而且,这芳香闻来似乎很是呛人,令人一阵阵地头脑发晕……
但他只是专注地梳她的发,并不曾留意自己的那点小伤。
他低低向她道。
唐天祺点头道:“可惜,可惜!”
给她一记击中心病,唐天霄顿时气急,压下她脑袋便亲住她的唇,缠绵半晌才恨恨道:“仗着你知我过去,我却不知你过去,你便处处欺负我罢!”
可浅媚却道:“我可不记挂你。得快活时我且快活着,才不自寻烦恼。”
可此处,除了鸦雀不祥的聒噪,便是这里那里不时传出的嘶嚎或呻|吟,宛若人间地狱。
他苦笑,紧窒包裹的温暖和愉悦让他重重地吐了口气,终于也说不出话来。
可浅媚深深呼吸着,想让发晕的头脑清醒些,却觉得更是晕眩了。
唐天祺等二人很快在刑跃文的亲自迎接下踏入密室。
堂上三人都怔住了。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