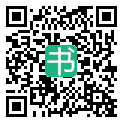第十四章 六月六日
成都的天,亮了又黑,黑了又亮。
高三的他们停下了脚步。
学校要发奖学金,宁玺算了算,那钱加上行骋家给的一些,两个人足够穷游一顿。
这个分数,宁玺肯定要读北大,全校人都这么认为,包括应与臣。
宁玺中午一起床,脑海里只记得一些零星片段,抓着被子下床,腿脚一软,腰上拴了件衬衫就往厕所跑,吐倒是没吐,就是有些头重脚轻。
这个成绩上北大,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
“好甜,哈密瓜的?”
宁玺站直了身子,弹了他一个脑蹦,任行骋拿纸为他擦汗,哼哼着说:“明年就该你了,你也加油。”
宁玺想起他高一入校的时候,对着这里充满向往与勇气,到了毕业的现在,仍然对着这一段时光有着美好的回忆。
应与臣正跟宁玺说着话,行骋冷不丁一句:“打得太久了,差不多挂了啊,你别念叨得我哥忘了古诗词。”
宁玺伸手去翻,高二三班,弄出来名单按首字母排的,第二个就是行骋,就他一个人,五个字:离北大近的。
他抬头看了行骋一眼,深吸一口气。紧接着是那种,释然的、终于放松的一声叹息。
“哥哥,你要去哪儿上学啊,我成绩差是差了点,但我可以努力。”
行骋边蹭边把他往人群外拖,喃喃道:“解放了,自由了,宁玺,我们都自由了……”
宁玺脑子里不断播放着那个数字,心脏一阵狂跳。
“哥,这球怎么那么圆?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抢一个球,买个新的不就得了吗?”
在这一刻,宁玺又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
他们不断喊过口号之后,单独在嘈杂声中喊了一遍校队要参加高考的学长的名字,助威打气,声音都快喊哑了。
当年的行骋和他,一个学渣一个学霸,一个高一一个高三,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看起来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
宁玺全程面无表情,只是客气地点头,夹菜,敬酒,喝到最后一点点地抿,抬头看着头顶挂的大红色横幅,“北京大学”四个字,刺痛了他的眼,一时间竟然没闹明白自己这天出席的目的是什么。
高考成绩下来的那一天傍晚,府南河边的余晖很美。
阳光有些刺眼,宁玺眯着眼看到另一栋楼的走廊上,教导主任和一群老师明知已经上课了,却也没有阻止这一场“喊楼”。
漫天的纸页落得差不多了,零零碎碎还有一些从楼上飘下来。
宁玺停顿了一下,还是说:“我觉得我考得非常好,应该没问题的。”
宁玺这话一出口,行骋想扇自己几个耳光。
他经历了复读,失落,打击,成绩下滑,乃至家庭纠纷,都挺过来了,因为他身旁并非空无一人,有老师同学,有教练队友,有应与臣,有行骋。
他这些日子也在考虑怎么样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好好多看他哥哥几眼,怎么去打持久战,但是没想到宁玺也在考虑,考虑如何能一直看着他。
行骋还没放假,但是都期末复习了,他们也正式成为了高三学生,平时上的课不多,自然空闲了不少时间出来陪他哥玩。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响了。
宁玺一紧张就容易去抓自己的衣摆,丝毫感觉不到衣服都皱了:“一年,四年,都太久了。”
感谢爱情,让他们在这最灿烂的季节拥有过最美好的时光。
“还没,明天去找个网吧。”
但宁玺总是这样,家长说什么就会去做,因为他明白,那是妈妈。
“梦想成真!放手一搏!”
两个人一起去参加街头品牌投篮大赛还赢了钱,夹娃娃夹了一堆晚上抱到夜市去卖,总的算下来,还是拿了几百块,宁玺开了个户,连带着之前攒的,全存进去了。
他这个分能读四川大学最好的专业,以后出来的话应该也还是好找工作,在成都的话……
红着,且甜着。
行骋猛地牵起宁玺的手,两个人没命似的跟着滨江东路的行人道跑,再往深了去,绕过草丛树林,不顾头上昏黄的路灯,不顾路人侧目,行骋一边跑一边大喊。
去考场的路上,两个人凑一块儿给应与臣打了电话,那边乐得哈哈大笑,说昨晚梦到考场上可以吃冰激凌,还很可惜没有在一个考点考试。
他也跟着跑下楼。
眼前蓝天白云,教学楼上站着自己最重要的人,手里拿着可以不断往前的飞机,宁玺突然明白了这架纸飞机的含义。
七号晚上,宁玺没有复习,骑了车跟行骋一起环着府南河边转了好几圈,折腾到了八点多,又蹬着车回去洗漱睡觉。
学弟学妹们还在喊着高考的口号。
高考发挥得很好在宁玺预料之中,但是这个成绩让他直接蒙了头,去年四川省的文科状元也就六百六十三分。
希望大家,明年也都不要再来了吧?
他最怕又最期待的事情终于出现了,他那么直接而强硬地影响了宁玺的生活,成为他的主宰,甚至会霸占他的所有,但是这种感觉又是如此痛苦。
是啊,人这一辈子就这么长了,“再见”“你好”,也就是四个字的事。
高三复读算是撞了墙,但是他感谢这堵墙。
行骋站直了身子,也不跟他多客气了:“哥,你真的相信我,我一定会过去的,我去天府广场搁那雕像面前宣誓,去府南河边许愿!”
应届毕业生们准备了好几个节目,又唱又跳,大荧幕上也不断回放着他们三年来的点点滴滴,好像就在昨天。
这几天还得抽空跟他哥去一趟医院看一下高原和_图_书反应,不然压根不敢往里面走。
宁玺妈妈打电话来问成绩,宁玺的语气不咸不淡,却也还是紧张,说要二十三号才能下成绩,这段时间,就先不用管他。
他这嗓子吼完,又传来一个低沉男音的一声咳嗽,吓得应与臣喉咙一哽,瞬间降低了音量悄声说:“我哥嫌我吵了,我先挂电话啦,宁玺,好好考。”
还有记者以为他是迟到的考生,满眼惋惜,忍住了去采访他的冲动。
他猛地往后倒退一步,看着宁玺手里的塑料瓶跌落到了地上,弹起来,滚至他的脚边。
行骋的语气里连劝带哄:“你先去北京待一年,我高考完了,就马上去找你,或者我有假期的时候,也可以来找你,成都到北京的机票打折的时候还是不贵,我都看过了,就五六百块钱……”
行骋现在所有的火气都上了头,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如果你要因为这个影响你读大学,那么你不用陪我!”
醒的时候是第二天,日上三竿,行骋坐在床边,拿手去掐他的小腿肚。
可大部分人就是这样,遇到了最后一个词,往往就昏了头,前两个通通可以不去考虑太多,只是与世无争地说着“顺其自然”,却不知道已深陷入泥潭。
宁玺看着回头等他的行骋,笑弯了眼,好想说一句谢谢。
都疯闹累了,宁玺边跑边往肚子里灌汽水。
离填志愿结束还有两三天,放了学行骋就找了家超市买好雪糕,两根哈密瓜味的,找了老板要冰袋装好,一路挂在自行车把上,穿过了小巷。
“你别犯傻啊玺,你一直想考北大我知道的……”
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脾气,怎么就口无遮拦,说了这么伤人的话,他慌着想给他哥道歉,又说不出口,瞪着眼戳在那儿,笨拙地抬起手,轻轻摸宁玺的后脑勺。
就好像成长忽然到了一个临界点,对前方充满期待,做一切都那么勇敢,有底气,不怕任何磨难。
宁玺的青春漫长而短暂。
他跟行骋余下的日子还有多少,他不知道。感情上,宁玺一直不是乐观的人。
即将面对的分离,就好像他欠了行骋一首手写的诗,而这个约定没有期限。
宁玺紧闭着眼,没搭理他。
宁玺看那纸飞机里面有字,便拆开看了。
那眉眼、那神情,看得宁玺喉头一哽咽。
他们没有喊宁玺的名字。
他们在校服上签字,认认真真把书全部收好,桌椅板凳摆得整整齐齐。
从小到大,行骋几乎从未在宁玺的脸上看过这样的表情,忽然心痛得不成样子,这一切都是他招惹的,小时候见过宁玺哭,那都是要么摔了要么磕着了。
行骋怕他哥吃辣坏了肚子就麻烦了,又跑上楼拿妈妈热的牛奶,后来怕早上高考交通不畅,行骋爸爸主动请缨,开着那黑色悍马,亲自把宁玺送到考场,负责接送。
行骋如今气急攻心,又觉得难挨,自责全转化成了哽咽,卡在喉咙硬是吞不下去。
行骋急忙拢了外套跟着追,眉一皱:“带我啊!”
“哥哥,你别不理我啊?”
行骋边跑边乐,他倒是稀罕听别人说他哥,感觉骄傲得很。
宁玺站在教学楼下往上望,看到全校的人都出来站在各年级的走廊上,纸飞机和横幅全拿出来了,混杂着高三年级从楼上扔下来的漫天纸页。
楼下的西瓜摊行骋天天都去,切成块,切成瓣,换着花样逗宁玺吃。
那一夜,宁玺在后面慢慢地走着,看着前面身形高大的弟弟,仿佛看到了十多年前那个小糯米团子,抱着篮球一边走一边倒退。
宁玺在教室多待了一会儿,走得晚,明显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猛地跑道窗边往下望,只听得到一浪高过一浪的集体呼喊。
“我知道了,妈!要得,晓得,没问题!”
他正趴在桌上往草稿纸上抄着什么,小台灯的亮度调到了最高,隐隐约约能照出他一截白的颈项。
上午十二点语文一考完,行骋紧张得很,眼睁睁看着他哥从考生大军里跑出来,站在门口可劲寻他,好在行骋穿的蓝色短袖,一眼就瞄到了。
宁玺咳嗽一声:“我还在考虑。”
他极少在外人面前露笑,可是这天根本控制不住,看到行骋他就心情好,想把这种愉悦传达给他。
老远他就看到行骋站在门口等他,这小子不知道怎么还挤到了家长团体中的第一排。
宁玺一伸手,把行骋的嘴给捂住了,憋着气骂:“你别说不好听的话。”
应与臣开了扬声器,那边一声吼:“平时怎么没看出来你变脸跟翻书似的呢!”
“宁玺,你听我说。”
“你带着你哥混什么呀,明天高考,你还耍得那么欢!过了明天你就高三了!”
“什么我管得宽?跟你同龄还这么近!”行骋直接咬下一口,给冰得牙齿发颤,眉一压,气势还有那么点唬人,“要我说这丫头就该再努力考一次北京……”
宁玺站在舞台幕后,透过厚重的暗红幕帘悄悄窥视着台下的一切。
好好学习,不仅仅止步于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应该是一辈子。
那天宁玺握着招生考试报看了很久,认认真真地跟他妈妈说,想报川大。
“宁玺哥,我现在篮球也打得特别好,你让我跟你切磋切磋呗?”
行骋晃悠悠地过去,双手插兜,认认真真喊了句“阿姨好”。
好像高考完了,他的心态好了挺多,天天有行骋陪着疯闹,一起打街球,夹娃娃,看电影,去特别小和*图*书的苍蝇馆子吃饭……
宁玺因为常年自己一个人睡,晚上睡不着便翻来覆去,有些惧怕这些东西,但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法医学今年的收分线。
宁玺刚吃完了晚饭,五六点的样子,正和行骋一起散步,往市中心的方向走。
他现在仍然随时都是能为了宁玺抡别人两拳头的毛头小子,但是更多的是学会了如何去为宁玺着想。
“那还是你被吃吧。”宁玺说着,也不废话了,去窗边抓过了一件黑格子衬衫披在身上,鸭舌帽反着往头上一扣,抓了口罩戴好,揣钥匙就要出门。
宁玺确定了要去北京,行骋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讲,都似乎化在了这甜甜的酒里,喂给宁玺喝。
“想在篮球场上,再看看你。”
多年后的宁玺,一直到大学毕业都还记得,那是高考临行的前一天,阳光明媚,铺满了操场上偌大的绿草地,像是在给予着他们一群即将奔赴战场的高三学子最美好的祝福。
这都是飞扬在空中的梦想,被夏季的烈日照得闪闪发光。
宁玺洗漱完回来手里拿了杯行骋泡的蜂蜜水,一口仰头干了,问他:“确定去阿坝州了?”
宁玺也开了口,给呛着了,咬着下嘴唇说:“你先讲。”
行骋点点头,没多说话,慢慢蹲下身子,把宁玺扛上背,随手从桌上顺了块紫薯糕含在嘴里,甜腻了一路。
宁玺喝得多,也记不得他搂着行骋的脖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唱:“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行骋揣着两根雪糕进屋,宁玺旁边添了个小电扇,呼啦呼啦转,吹起他的招生考试报边角。
回家已是深夜,宁玺就着一地月凉如水,缠着他喊“弟弟”的场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哪怕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不是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在一起,整个考点的考场内都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
妈妈打了一千块钱过来,宁玺给认真收好了,说以后留着用。
后来的行骋和他,从平行线变成相交线,互相追逐纠缠。
宁玺解释完了,拿着手机,慢慢站起身来,把套头衫的帽子取了。
行骋像是叹气一般地努力让自己的情绪镇定一些,仰头深呼吸,攥紧了拳:“你别不信我。”
宁玺急忙把听筒声音调小了些,那边忙着拆外卖的行骋像没听到这句话似的,看他哥朝这边望了,还笑着点点头。
暑雨初晴,学校院墙边蔷薇满架,好似吹了一操场的香。
宁玺在后面跟不上脚步,面上挂着笑,听行骋一转头,对他说:“哥,走,去北京上学了。”
“哥,你看看我。”
“我一想到,”宁玺说,“去北京的话,可能我一个人生活,很难。”
行骋还不知道这些事情,满门心思都扑到怎么带他哥放松心情上面去了。免不了挨爸妈一顿骂:“你看看你能考多少分,再看看人家,甩你八条街!”
六百六十分,刚好还凑了个整。
“你可以说我脑子不清醒,可以说我现在太不理智,但是你不能……”
“我……”
前来祝贺的家长,感慨万千的老师,以及坐在高三席位最中间,一直不肯离去的行骋。
决定放弃西藏是行骋想了很久的,毕竟就他跟他哥两个人一起,在那边落了单不太安全,反正以后机会也多,多跑跑也没事。
志愿截止的前一天,行骋猜都猜到了他哥要等到时间快到了才会去网吧,直接翘了一天的课要跟着,得看着那志愿表交上去了才作数。
高三四班宁玺,请金榜题名。
宁玺抓起手边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喝了口,才镇定下来,他掐着瓶身的手都有些发颤:“我想报川大。”
有一次他看高二传上来了学校要求填的理想大学登记薄,人家每个同学,写大学名字写得规规矩矩,清一色的“xx大学”“xxx学院”,他在办公室里瞟了好几眼,没忍住问老师能看吗,老师下巴一抬:“你看。”
行骋一听,愣掉半秒反应过来,确认一遍:“四川大学?”
行骋在后面愣着喊:“哥,你上哪儿啊?”
“你去府南河起个什么作用。”
恣意,快活,连纸飞机携来的风中,都带有甜味。
好像天女散花……
用力爱着,再接再厉。
行骋憋着不吭声,为什么决定去金川县的云顶花海,因为那儿能看星空不说,还是夏日露营的好地方。
宁玺把草稿纸上的重点画好,合了笔盖一下敲上弟弟脑门,佯怒道:“你管得宽。”
行骋端着饭菜走过来,在小桌子上铺了报纸,招呼着宁玺坐下吃饭。
七号一大早的,行骋很早就起来了,从楼上给他哥端了妈妈煮的蟹黄粥下去,宁玺想拌点老干妈喝粥,行骋不让,抱着那一罐老干妈视死如归。
关乎人生,关乎命运。
宁玺居然感觉到了喉头的哽咽,他拼命咬着牙把那难受的痉挛感强压下去,睁大了眼:“不能说,你不要我陪。”
宁玺听他弟说这话,除了想骂几句他犯浑,心底还有丝丝愧疚,他压根不知道怎么告诉行骋,他想报川大。
宁玺没有想过他楼上的小屁孩弟弟能长成了这个样子。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
两个人拿着一个勺子躺在床边,去看今晚的月亮圆不圆。
“宁玺!”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代表他的这段青春,那大概就是行骋带领着一群校队的战友在教学楼上为他呐喊的模样了。
那晚上的月亮挂得很高,宁玺看得晕晕乎乎,最后就那么趴在饭桌上睡着了。
行骋在日历本上hetushu.com.com重重画下一个圈:“八月八日,就这天出发吧。”
他抬头看向行骋,感觉眼底热热的,像有什么情绪要夺眶而出。
行骋忽然想到什么似的,一边收拾垃圾一边问宁玺:“你初中学校让你去给高二的发言,想好说什么了吗?”
在大部分高考学子心中留存过的梦想,他宁玺,终于在二战了一年之后,将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收入囊中。
难受是难受,宁玺一张俊脸还是垮得厉害,招牌式的冷淡表情又挂上了面,屈着手肘去推行骋,不想再多说什么。
以前他们高三的时候他就特别不能理解一些女孩子男孩子,为什么会因为另外一个人去做影响自己人生的决定。
宁玺闭了闭眼:“能。”
宁玺一笑,傻不傻啊。再怎么也得是他乘飞机回成都来找行骋啊,哪儿有高三了还到处乱跑的?
这天提前放,下午只用上两节课就可以走了,大家却舍不得似的,站在原地,有的女生哭了,有的男生,也哭了。
宁玺捂着麦克风没忍住大笑,说:“你也加油。”
行骋进入了高三,暑假放得格外短,七月中旬放的假,差不多八月底就得返校,这还是他选择了不补课,像任眉那几个被家里逼着去补课的,得到八月初才能放。
行骋随口一问,舔了点尝味,宁玺手上的笔没停歇,回答他:“我妈那边亲戚的小孩今年考得不好,让我帮忙看看学校。”
宁玺手里本来就拿着给行骋的那一只口罩,边拆包装边走过来,双手扣住行骋的耳朵,轻轻把口罩套了上去,捏了捏他的鼻梁,说:“最近成都雾霾严重,别给捂傻了。”
本来这一天,行骋的神经就高度紧张,看他哥这样子一愣,颈间有些湿热的液体流下,更吓得他动都不敢动,狠命抱着他哥,往桥边,一步步地挪。
这几天为了填志愿的事跑了几趟学校,教学处的老师轮番给他做思想工作,连应与臣身在北京,都每天几个电话。
他正想说这桌子质量还不错,用了大半年都没坏,下次再往家具城走,再捎一个,拼个大的,吃吃满汉全席……
包括钱、学业、家庭,乃至是感情。
挥洒过汗水泪水的塑胶操场,天空中成群结队飞过的鸟,教学楼前从不枯萎的小花,走廊拐角处总是趴在地上晒太阳的猫。
六月即将过去的那一个周末,石中举办了毕业典礼。
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会不会有一天时光真的能倒退,到他回不去的悠悠岁月。
他没再多说,慌着直接挂了电话,恢复一贯冷淡的表情,把手机调了静音,再像没事人似的,给应与臣发消息。
甚至还画了个箭头符号,是成都到北京的。
笑到最后,开始哭。
应与臣的声音提高了八个调:“你不会要为了行骋那臭小子读川大吧?你明年让他自己考到北京不就成了吗?”
他们两个人,穿着短袖背着书包,一起过了考点门口的马路,朝着停在不远处的悍马跑过去。
行骋跟屁虫一样跟到了考点门口,美其名曰提前感受气氛,其实就是背个黑书包在门口等着,拿着矿泉水、纸巾,一米八几的个子立在家长中间,活像棵小白杨。
录取通知书下来的当晚,宁玺妈妈和后爸开着车来把宁玺接走,找了饭馆请了些亲朋好友吃饭,收了不少礼金。
行骋走过去把雪糕拆了递到他嘴边:“哥,你怎么开始看湖北的学校了?”
行骋拿着雪糕喂他,自己也吃:“男孩女孩?”
行骋的怒意和难受的感觉齐齐涌上心头,他不想耽搁到宁玺半分,大学对于宁玺这种家庭的小孩来说,真的足以改变他的一生。
行骋捧了本旅游手册在一边拿着荧光笔勾勾画画,他怕是平时学习都没这么认真过,边看边念:“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雄踞在四川省西北部……”
宁玺那么清楚,能独自一人去外地念四年书代表着什么,脱离父母的管控范围又代表着什么。
什么事情都要方便一些。
应与臣那边正在北京玩得嗨,天天在家玩了还不够,呼朋唤友,乐得自在,宁玺还真想不通,应与臣怎么就要读川大了,毕业之后那不还得回北京吗?
宁玺回想起自己偶尔上课用手机看NBA的文字直播,下课就到处有人串班,站在走廊里面对着打闹的男孩,对着小镜子画眉的女孩……
宁玺没半点犹豫,当着这么多考生家长的面,不去管横幅上大大的“高考”二字,也没顾着有没有媒体采访在门口举着摄像机候着,就那么在家长们的激动与焦急中,跑到了行骋身边站好。
“行骋,我必须跟你说一件事。”
如行骋所愿的,宁玺八号发挥得很轻松,考场上没打瞌睡没走神,认认真真做完了题,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应与臣纳闷极了:“你问这个做什么?”
时光伴随着夏风,毫不喘气地朝着六月狂奔而去。
宁玺应当是明白的,只是点了点头,眼不自控地红了一片,嘴角因为难受的缘故,颤抖着往下撇,也没再说话。
今年石中考得还不错,重本率特别高,学校领导和老师心情好得很,这段时间对高一高二的管制稍微松了些,行骋常常上课往窗外望,心底期待着暑假。
宁玺想不了这么多,想不了什么以后生活如何如何,他只知道他受不了长时间见不到行骋,他现在只看得清眼前,甚至近乎偏执地想要去抓紧,再抓紧一些。
在这之前,他没想到过,他https://www.hetushu.com.com有一天,真的会因为别人去动了择校的心思。
行骋眉眼生得俊朗,身高出类拔萃,站在那儿像个标杆,见一帮弟兄都没喊了,他忽然把手举起来,朝着宁玺的方向大吼一声。
他的手机收到了教育局的简讯,那时他只当是别的简讯,只是把手机拿出来。
“哥,”行骋开口,“我知道你是因为我。”
等成绩的日子,漫长而无畏。
行骋见宁玺不说话,哄着他把手机拿过来看了,一激动,不小心扯了河边垂了半截的柳枝,心里没太大个数,又兴奋又纠结地问:“哥,哥,你这个分,能不能上北大?”
手腕上的青筋看得明显,较高的身型在门框上隐约投下剪影,连他侧脸上的轮廓光线,都将他的气质勾勒到了极致。
行骋哑声道:“我想要你什么都好,样样优秀,不会为任何烦恼……”
班主任挨个数落着班上的同学,告诉他们高考的注意事项,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甚至还开始调侃起来,不少同学都笑到了桌子下面。
“我忽然好想回到高中。”
一抬头,就听到宁玺正在对着自己讲话。
应与臣转了学成绩依旧好,机灵劲全用到了学习上,高考考得也很不错,六百三十七分,说刚好可以读个川大的法医专业,也挺好的。
宁玺解释不了别的,千言万语根本出不了口,慢慢地松开攥着衣摆的手,面上仍带着似乎不化的冰,咬牙道:“读大学是我自己的选择,可能北大不适合我。”
“府南河里的僵尸你没听说过?要是我考不上,它们就全跳出来吃我……”
高三人不多,考得大部分都不错,挨个上台领了奖励,宁玺站在最前面的一排,着统一的校服,下巴微微扬起,皮肤越发白净,眼眸眯着,总带着些没睡醒的意味。
一转身,傍晚的余晖在宁玺身边都画了道剪影:“吃饭啊,到点了。”
第二个数字是也是六,第三个数字是零。
行骋像是一下被打得闷头一棒,人都还有点不清醒,问他:“为什么?这分上不了北大?”
最后一节课,依照往年的规矩,班上所有同学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黑板上,班主任泣不成声,辛苦了三年的班委全部起立,领着同学向她鞠躬。
行骋闻言直接把他抱起来转了一圈,像条大狗似的撒欢。
昨天那家饭馆,偏僻且远,都没在青羊区,行骋硬是问了好多人才打听到,摸过去的时候,宁玺妈妈站在宁玺旁边打电话,满眼焦急,催着她男人来把儿子抬回去。
宁玺拗不过他,这段日子心里也安心了不少,加上应与臣那边一天三四个电话地教育,只得顺着最开始的意思,报了北京大学。
高考成绩一公布,匆忙的毕业季到了,成都的天气又热几分。
宁玺又喝了一口柚子茶,嘴里酸甜的味宁玺很喜欢,他舔了舔嘴角:“你别担心。”
行骋憋住笑,去把被子往上掖了些,拇指轻轻地刮他的侧脸,接道:“你这是要温暖谁的心房?”
整整三个月,他都还没想好要怎么过,跟行骋约了七月底进阿坝州或者甘孜州玩一回,八月份也还想跑一趟海边。
那墙根还留着宁玺小时候留下的脚印。
这些都是借口,宁玺想说的不过只是一句“很难见到你”罢了。
瓶身被宁玺捏得变了形,他深吸一口气,点点头:“对。”
头顶的追光打得很亮,台下几乎座无虚席,那一瞬间,宁玺觉得,他似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切。
宁玺小声说:“你不说我就问老师去了……”
行骋希望,宁玺在北京的时候,如果哪一天特别想他了,那回忆一定要是石榴味的。
应与臣真的气坏了:“考虑什么,志愿都填了吧?”
行骋约了队里两个阿坝州的朋友,刚好住在金川那边,说到了好有个接应,行骋只恨自己年纪不够还学不了车,不然早开车进藏区自驾游了,还坐什么大巴车。
行骋站起来把塑料袋打包装好,继续道:“好像是周二,我下午课少,应该可以逃一节去看你。”
行骋假装正经地咳嗽一声,这火气莫名其妙就没了:“你是舍不得我被他们吃。”
他永远记住毕业典礼上面年级主任的致辞,前途正是因为未卜,所以无量。
七号、八号,宁玺高考考了两天,石中作为青羊区的考场,全校也放了假。
他抬起眼去看窗外那些欢呼雀跃的考生,看他们抹眼泪,看他们头也不回地离开,离开他们人生中,最后的高中教室。
那会儿的行骋和宁玺,高考结束之后连着疯玩了好几天,全市大街小巷都逛遍了,一天骑了三十多公里,第二天两个人屁股痛得躺了一天。
行骋认认真真地把旅游路线给他哥讲了一遍,宁玺只觉得吃的还挺多,其他都随着行骋去安排了,住宿也确认了一下,瞪着眼问:“没定旅馆?”
宁玺一出考场,走得很急,急到一边走一边扔机读笔,扔中性笔,最后把准考证和身份证往书包里一揣,朝着考点门口飞奔。
行骋妈妈一见着行骋顶着满脑袋汗回来,戳着他的脑门就开始骂。
偶尔开瓶百威啤酒,行骋一口扯了一半下肚,嘴里含一口加了冰块的酒,舒坦得直哼小曲,拿起吉他就想弹点什么。
一提到钱,宁玺就沉默了,他不得不去想前段时间行骋打黑球赚钱给他买东西的事,这简直是他心底一根刺,隐秘而疼痛。
只是匆匆地看了一眼。
宁玺带着笑站在原地,仰着头看行骋。
那一天的毕m.hetushu•com•com业典礼,在欢呼声和哭声中谢了幕,那是他最后一次穿着校服,和行骋遥遥相望。
三位数,六打头。
他生命中的四年就这样没有了,下一个四年在大学,那下下个四年,又将要在哪里?
他们逛到锦里尾巴上,行骋看见了店家卖的酿酒,又买了两瓶石榴荔枝的,两个人边走边喝,差点儿被一口甜味齁死。
没有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是什么离不开家乡,只是因为行骋而已,只是因为他离不开他弟弟。
宁玺没吭声,皱着眉在听。
宁玺提交的时候,眼看着网页刷新成功,手都在抖。
宁玺妈妈这一下还没认出来小子是谁,看清楚了才犹犹豫豫地开口:“哎哟,这不是行骋吗,来接宁玺的?”
他们好像天生就是一体,是散落的两片拼图,非得给凑上了,各自才完整得了。
行骋仿佛在跟自己讲话:“我说过会去北京找你,那我肯定会来,也会努力考过去!”
他一下就看到行骋那一群兄弟,十多个大男孩,都脱了校服,穿着统一的红黑色篮球队队服,把校服绑在胳膊上,全部举了起来,一个劲地乱挥。
宁玺坐的靠窗的位子,他记得那天的阳光很大,把试卷都烤得有些温热。
宁玺想了无数句坦白的开头,但是没想到自己脱口而出时显得那么慎重,他慢慢站起身来,把那一袋垃圾轻轻放在门口,把愣住的行骋推进了屋,随手关上门。
教室里的同学终于开始要陆陆续续地离开了,不少人已经走出了教学楼,忽然听到楼下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开始为他们喊楼。
现在他彻底明白了。
从这天开始,宁玺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自由了。
两个人一起喝着汽水流着汗水往街对面停着的悍马上跑,行骋爸爸问了一下情况,宁玺信心满满,说没多大问题。
而他们的两颗青葱少年心,发着热,也发着光。
宁玺也只是扯过来拿钢笔一下下地描那些字句,再撕下纸揉成团,任他们碎成片。
宁玺猛地一愣,目光迅速锁定在行骋身上,紧接着,他听见校队剩下的学弟们跟着行骋的指挥喊道:“金榜题名!”
可能每一届的学生,都是在彻底要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才真正地爱上这里。
“石中牛!”
他忽然意识到,长大是慢慢变成独处,是发觉自己永远没有长大,就好比他一对上行骋,就永远是那个童年时,在卧室窗前写练习册,却望着零食从楼上掉下来的,发呆的小哥哥。
行骋笑着,一使劲,从高二的楼层飞下来一架纸飞机,像是拿大纸叠的,不偏不倚飞向宁玺的方向,宁玺跟着跑了几步,伸手接住。
其实行骋一望进他哥的眼神,他是能猜到一分半点的。
宁玺的成绩,毫无疑问地又成了同学之间的议论热点,毕竟四川省今年的文科状元出来了,在一个外国语学校,比宁玺多了八分。
“我想你永远陪着我,但是,我不想因为我去影响到你该走的锦绣前程,”行骋的目光紧紧锁着宁玺的眼,生怕那里面的水悄悄溢出来,“你明白吗?”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他哥哥一直想读人大和北大他是知道的,这次高考也发挥得非常好,这个分按理来说不可能读不了,他也是知道的……
成都的芙蓉花每一年都会开,人也会永远是当初的少年。
上交了志愿表的当天,行骋骑着自行车跟宁玺跑了一趟锦里古街,两个人进去的时候还是饿着肚子,出来就撑得不行了,虽然说一般情况下,成都本地人很少去那儿,但偶尔去一趟倒也还不错。
只那么一瞬间,宁玺像是浑身脱了力一般,一下转过身,在大街上,不管周遭有多少散步的人,直接把行骋抱住了。
行骋的导火线本来即将一点就燃,但一听到他哥说的那句“生活很难”,心一下就软得不成样子。
高考过后的夏天太美好。
他张嘴,摸不清现在行骋的情绪,只得慢慢地说:“我如果读川大,很近,一两公里,骑自行车,不花钱。”
“西藏太远,川藏线这时候旺季,我们去茶店子客运站那边坐车往里面走就行,阿坝州还算安全,我有几个同学家也在那里。”
宁玺浑身都僵硬了。
有些面孔今后也不会再见了,有些故事永远不会再继续,但是都有梦想,都不会止步于此。
两个人沉默一阵,都憋着气,行骋刚想开口:“我……”
行骋一下把头抬起来,盯着宁玺家里那刷得雪白的墙壁,想一头撞死上去。
宁玺的个子高,站在一大群高三的人当中十分瞩目,他正急着在高二那一层的走廊上寻找行骋。
逃课喊楼,现在的时间应该是要上课的。
校服都还没来得及脱的少年拎着一塑料袋的雪糕棒,吃完的番茄薯片包装,手里拿着小扇子,正对着他笑。
北京。
这样红着眼不讲话,是第一次。
行骋倒是紧张得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翻来覆去的,明天一上午的考完,下午稍微轻松些,考完了就真正解放了,等明年这个时候,自己估计也能一冲出来,就去北京找宁玺……
互相折磨,互相影响,互相成长,哪怕有些步骤,从一开始就错了。
腋下突然像生出了双翼。
行骋一边点头一边求饶,提着鞋往卧室跑,脚底跟抹了油似的。
宁玺见不得行骋这样,书都不看。天天在家里待着看杂志看小说,偶尔随笔写两句。
就一排小字:“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至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