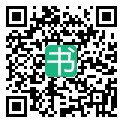第十八章 夜归人
宁玺幼年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爸爸去世,如今再次踏入医院,再找到住院部,迎面而来的是满鼻腔消毒水味,连带着病房里全是,摆再多的鲜花也掩盖不了那股气息。
“行骋。”
宁玺特别惦记去年在北京下楼“拿快递”那一瞬间的心情,就好像天降惊喜,那满世界落的都不是雪,是飘下界的云朵,来领着他和行骋回家。
前面还坐着爸妈,行骋把宁玺的手心拖过来,用指尖在上面写字。
现在如若爸妈还要问起,行骋特别想说,结果了,也落叶了。
“呃……”
“对,你下去睡,让宁玺上来住。”
程曦雨兴高采烈地一走,宁玺瞪着行骋:“他明天跟我们约了。”
行骋的家里面宁玺有一段时间没来了,落了座就端端正正坐在板凳上,看行骋爸爸喝大碗茶,一五一十地回答问题,大多都是关于大学生活的。
饭吃了一半,桌上宁玺帮着摆盘又夹菜的,看得行骋胸口堵得慌,他抬眼去看他哥的表情,分明就是完全放下了平时的“架子”,卸掉那层保护膜,认认真真地想要靠近。
宁玺眼看母亲再婚,脱离他的生活,再到有了自己的家庭,后来偶尔的关心与问候,虽然很小也很少,但还是抓紧了他那一处敏感的神经,每每一被碰到,就好似陈年旧伤,往上浇酒精,撒盐,都抵不得这种痛楚。
冬日的夜,难得有此间澄明晚景,天淡如水,月亮挂了梢头,被城市的霓虹倒映出晕染开的紫红。
行骋觉着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没说错。”
宁玺一颗心全扑到学校门口去。
他突然站起身来,从兜里摸了一个纸包,趁着医生给还在沉睡的妈妈检查的时候,把那个纸包塞到她的枕头底下,又在床边站了一会儿。
应与臣说要一起去看,问他捎不捎上行骋,宁玺只说行骋要念书,一大早就看到行骋背着书包出门了,天都没亮,手上拿了盒奶,衣服也穿得不够,估计被冻着了。
宁玺的心太软了,也只为他在乎的人柔软。
宁玺回来第一晚,不好意思把行骋留下来,只得以累了为借口,待两个人收拾好房间,卫生也弄完之后,才催着行骋回家。
阳光洒到宁玺的睫毛上镀了层金,行骋看得呆愣。
宁玺归心似箭,一步并作两步,他只想快些。
这一年的春节来得很快,大年二十九,行骋从二楼往一楼飞奔下来,忙着去敲宁玺的门,一打开,行骋拎着宁玺转了一圈,看上看下,“今天一看就讨我爸妈喜欢!”
宁玺觉得她很眼熟,想了一会儿才记起来是之前在玉林路跟行骋他们吃夜宵打了架的女孩子,校篮球啦啦队的。
一月底,寒假。
行骋仿佛化作了这小舟,载着他朝家乡的方向奔流不息。
差不多十小时后,宁玺终于到了成都,整个车厢都像苏醒了一般。
行骋虽然大冬天一早就被亲妈给关在门外守班,但心里头暖得热乎。
行骋爸爸站直了身子,一挥手:“行骋,我们带宁玺去外面吃更好的。”
“我也会。”行骋跟着他讲,“但是,我希望你只经历前两个。”
或者是,他在这里等了多久?
宁玺无奈,训他:“你真的疯。”
大门被妈妈关上的时候,行骋听他妈妈咬牙切齿地讲:“你翻窗户不是挺厉害?继续折腾,摔断腿了看你怎么考试!”
行骋被推搡着出门,回过头来询问:“那还吃喝玩乐吗?”
宁玺刚感动了一秒,这会儿就想把花插行骋头上,天天玩个翻天覆地的,还考不考大学了。
行骋不知道从哪里变了朵黑玫瑰出来,插到那束花的最中间,说:“这叫,只有我一个。”
他渴望而畏惧,同时承担着这份责任。
也就是大年初一一大早,行骋或许是还记得小时候干过的那些蠢事,抱了一小束花,站在宁玺家门口给他:“这花语叫勿忘我。”
宁玺推开门,迎面撞见出来倒垃圾的大姨,没喊,目光全锁在病床上的妈妈。
程曦雨顺着行骋的眼神望过去,喜出望外,先开口喊他:“玺哥!”
宁玺的生活中,与长辈打交道的时刻屈指可数,更别说是“叔叔”“阿姨”之类对他来说算是亲密的用词,他现在在乎行骋父母的态度,落了碗筷在桌上,不敢再动那些菜盘,行骋妈妈和行骋也停下了。
妈妈把盛了大碗骨头汤的保温碗用保鲜膜覆了,拎袋子递过去:“你今晚还回来住吗?”
昨晚除夕,奶奶回县城里了,行骋趁着这年家里就他们一家三口吃团年饭,跟爸妈说了宁玺家里的事,三个人沉默一阵,谁也没说话,行骋倒也安静,等他爸开金口。
后来宁和图书玺回到房里,又偷偷在备忘录上记了一笔。
“但求同年同日再买两瓶红石榴汽水,一起喝到落日夕阳无边醉。”
那天宁玺没有去问,行骋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是不是应与臣告诉他妈妈生病的,是不是逃课了,是不是回去又被抓住训斥了……
宁玺的脑子转得快,听懂了什么意思,瞪他:“你不要没事找事。”
宁玺自从跟行骋一块儿之后,扪心自问,开朗了不少,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连带效应,似乎都在互相影响着,他能感觉到行骋的成熟与日渐稳重,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心门,慢慢地以一种平和乐观的心态,在对待一些人和事物。
四个人凑了圆桌,行骋妈妈端碗给宁玺盛米汤,笑容还是宁玺记忆里那般:“你小时候就爱喝,行骋爱显摆,有点好吃的就在外面啃,招人恨!”
“怎么了?”宁玺还有点蒙,“叔叔阿姨怎么了?”
宁玺从医院回来就犯困,他还是每天都会去石中跟行骋碰个面,偶尔给他带点饮料,行骋会高兴。
“给你闲的。”
行骋听见宁玺压低了嗓音,有些犯哑,手攀着他的胳膊,说:“我把攒下来准备在北京租房的钱,给我妈了。”
行骋再次见到宁玺妈妈,都有点记忆模糊了,似乎他记忆中那个蛮横刻薄的女人,不应该像这般躺在病榻上,戴着帽子,憔悴不已。
宁玺也乖,一遍又一遍地去掖不漏风的被角,说有开,妈妈问冬天也开吗,宁玺说,也开的。
他背上背了个篮球袋,里面一颗Spalding(篮球品牌),藏蓝色皮混着黄,上面印了NBA雷霆队的标。
行骋见宁玺埋着头不吭声,伸手去揉捏宁玺软软的后颈:“生老病死,都逃不过。”
宁玺一整天都好像在黑暗里摸索寻找,如今行骋突然出现,像一束追光,彻底点亮了他的前方。
宁玺嘀咕:“你怎么不画我的脸啊?”
初五倒是轻松了些,大姨那边过完年回来帮着照看妈妈了,宁玺破例在家里一觉睡到中午,等阳光都从窗户外进来晒屁股了,才听到行骋站在他一楼的窗户边喊他,手里提了两瓶汽水。
宁玺把衣服的扣子扣好了,对着在嗑瓜子的女人低声说道:“大姨,我明天再来。”
“这在大街上……慢点!”
宁玺正想过去喊行骋,反倒是行骋个子高视野广,跟座瞭望塔似的,脑袋四处看了看,一眼便看着了他哥,整个人都愣住。
本地女人说话难免带些嗲气,倒是要被儿子给气得想笑,开启了一波行骋无法反驳的攻击:“你想得倒挺美?你考得上北京吗,你那个成绩,念周边吧?每周骑你小破三轮去北大找宁玺,小心他同学往你箩筐里扔废品!”
大姨回过头来看他,宁玺只是说:“谢谢大姨,我吃不下。”
“我怎么没听见过?”宁玺嘴硬。
宁玺说:“给你一个惊喜。”
宁玺的瞌睡一下子醒了,抬起一条胳膊,放在行骋的头上,像摸小狗似的哄:“不会腻,傻子。”
“我们?你提前跟他说你回来了?”
程曦雨知道这哥俩好,没想过别的,拖着宁玺的胳膊就求他:“玺哥,你能帮我把应与臣约出来吗?”
行骋一笑,笑得有些勉强了,提到这种沉重的话题,劝慰般地说:“那就,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说关系也还挺好,是哥们,但行骋爱吃醋改不掉,免不了偶尔说几句。
他一边拼了命地长大,又一边没了命地失去着。
去年行骋挤在这处扇自己耳光的情景历历在目,宁玺忍不住问:“你自己扇自己耳光扇上瘾了?”
宁玺忽然一种无力感从心底涌动起来,经历过直系亲属的离开,他明白死亡不是简单的一瞬间。
行骋从兜里掏出一部手机看了一眼,又皱着眉把手机塞回去。
最后一段路,行骋实在累,没坚持下去,感觉他哥都要滑下去了,才放下来,宁玺站在小区不远处的街角,又看着行骋跑得像风中一匹狼,折回去拿自己的行李箱。
宁玺瞬间没了话语,只得生硬地问:“哪个医院?我打车来。”
一个箱子,里面装了些换洗衣物,几袋特产,三本书。
这一趟车开得很快,领着宁玺他淌过山川湖海,辽阔原野,好似一条南归的江河,自北方匆匆而下。
“没事,”行骋不假思索地答,“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承担。”
他当时傻在那儿,点了点头,还是埋着头吃。
她不等行骋回答,抬了抬手里的罐:“喏,给宁玺拿点去,我看他读个大学都瘦了,心疼得我……”
“哥,你说。”
宁玺m.hetushu.com.com精神了点:“你就这点出息?”
宁玺回到那条他熟悉的街道,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拖着箱子往石中的方向走,行李箱的小转滚一路有些响声,下晚自习的全是高三的学生,都匆匆往家里赶,过路的行人偶有几个回头看他,他压根没注意到。
晚上这一觉睡得舒坦,宁玺一个人躺在床上,闭上眼,满脑子都是行骋那会儿翻进窗户,蹲在他床边,脱衣服或是穿衣服,连趴书桌上写字的姿势,都顺眼。
行骋现在胆又养肥了,捏着他脸:“窗户都快被我翻塌了,我当时就在想,你怎么还对我有意见?”
行骋跑过去把宁玺手里的箱子拖好,人还是傻的,他哥不是还在北京上着课吗?
“那是蝎子,寓意是你,我再强调一遍,”行骋喘着气,“我直接写你名字成吗?”
宁玺还没说话,倒还有个短发女孩从一侧绕过来,喊了行骋一声:“行骋!”
宁玺闭了闭眼,没说出这句话。
只是一个下午加傍晚,行骋的寒假作业就在宁玺的监督下又写完三张试卷,两个人弄得腰酸背痛,偷懒睡了三小时,才又爬起来,挑灯夜战。
行骋嘴角没忍住勾起来了,又说:“不都是在当事人不在的时候,才起哄吗?”
宁玺差不多坐到下午三四点,医生来换药,把床上病人蒙了半边脸的被褥和毛线帽揭开,宁玺才看清楚,妈妈已经把头发剃了,还在睡,没醒。
父亲的死亡并非在那一瞬间,那一天,或者那一日,而是从头到尾,贯穿了宁玺的一生。
看到行骋这个动作,宁玺才想起来,他在车上睡着之后急着下车,再赶路,也没来得及回行骋的短信。
年后的时间过得很快,大年初二,行骋一大早爬起来跑去小区门口的水果店买了果篮,也没跟宁玺打招呼,到小区单元楼下等着宁玺,跟着一块儿去了医院。
宁玺打球,跑步,成绩优异,几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绩要拿第一名,打球要打成MVP,就是觉得是爸爸把生命的余额交到了他手上,岁月不容得他浑浑噩噩,更不容得他原地踏步,他只能选择拼命地跑,去踏山河千川,去全力拥抱他的人生。
“妈,我怎么没闻到,”行骋站起来,乐得很,“您对我哥怎么这么好啊?”
看行骋真的有这打算,宁玺趴在他的背上,心里要乐死,还是严肃道:“你去安个LED屏,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循环播放。”
行骋妈妈把罐子一放,抽出手去推一把行骋,涂了甲油的手朝厨房灶上煲汤锅里指:“你想什么呢?那儿锅里大骨头汤,我熬了一晚上,味道香得你爸半夜都起来了!快,你端下去。”
这惊喜的确是惊喜,行骋在校门口就把宁玺扛起来转了一圈:“你是惊喜中的惊喜!”
行骋爸爸点了根烟,往里面加上沉香,满屋子闷得熏人。
行骋看着他妈妈手里的罐子,皱眉问道:“这个?”
那天宁玺拿着手机在窗边站了很久,才给应与臣发短信,说这天怕是没办法赴约了,要去一趟城周边的医院,妈妈生病了。
他哥这是提前回来了?还是他产生幻觉了?
行骋朝宁玺那边挤了挤,他意会,微微侧过身,就半靠在彼此身上。
这一路,宁玺用尽了力气,去同行骋相互搀扶着成长,前方等待的是什么,他也不想知晓。
“好,”宁玺一下就紧张了,任行骋捏他,“但明天才是除夕啊。”
“我也想要以前的味道,”行骋笑了,“那怎么办啊?”
“吃不下了,”行骋爸爸仰头干完了大碗里的茶水,站起身取下衣架上的厚棉衣,“走。”
宁玺从小身体还不错,极少去医院,家里人也没怎么操过心。
宁玺几乎是跑着出住院部的,下了楼梯又在一棵树下站了一会儿,冷风呼啸而过,吹得枝头落叶洒洒,他想起那句“树欲静而风不止”,下一句却再不愿意去想了。
宁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行骋蛮劲扛背上了,少年有力的臂膀反手托住他的身体,宁玺迅速罩上帽子只露出一双眼,半眯着四处看,还是那副睡不醒的样子。
母子之间的交流依旧很少,妈妈也不太爱讲话了,只是常躺在床上,闭着眼,问宁玺,五楼秦家的花,今年有开吗?
宁玺没躲得开,嘴角被塞入颗湿漉漉的提子,酸甜带涩,卡在那处,就是吞咽不下去。
那女孩这么冷的天手里拿个雪糕,校服裹得暖和,双颊红扑扑的,跟在行骋身侧一步步地走,嘴里说了什么,宁玺听不见。
“您不是老在家里念叨吗,宁玺要是我儿子就好了,行骋你看看你自己,像个什
m.hetushu.com.com么德行!”行骋学他妈妈说话,被擀面杖拿着敲了脑袋,边躲边笑,“这下真成你儿子了。”宁玺:“呃……”
行骋一听这话,跟被幸福砸晕了头一样,傻了:“我还能不回来?”
大姨电话一来,说是离婚了,他那个开着二手小宝马的后爸带着弟弟走了,估计下了哪个周边卫星镇去,没待在市里,宁玺完全愣住了,他没听见半点风声,每个月那点生活费虽然不多,但还是照常往卡上打,得了病这事,没人跟他提,他也没想到过。
“别说了,”宁玺强硬地打断她难以入耳的话语,“我过去。”
最后得出结论,就三个字:又一年。
“啪”的一声筷子碰碗壁的响声,行骋爸爸紧皱着眉,不吭声,而宁玺几乎同时间,喊了声“行叔叔”。
直到他走了一截,望到门诊部门口站着一个人,喝牛奶喝到了一米八七左右,校服湛蓝,脚上一双球鞋战靴,书包都没背,正四处张望着。
或许是那边听筒的电流声大,宁玺费劲地听,大姨在那边拿着电话一阵吆喝,倒像丝毫不觉得患病的是自己的妹妹:“你是不晓得你妈妈,宫颈癌,之前就说身体不舒服,去检查的时候,都中后期了,没活头!”
宁玺还没走到校门口小卖部的地方,老远就从人群之中瞄准了比挺多人都高半个脑袋的行骋。
宁玺趴到窗边,睡眼惺忪,几乎又要困得睡了。
给了小区院墙后面的爬山虎,给了在他面前胡闹捣蛋的跟屁虫弟弟。
宁玺也在学着,在别人很热情的情况下,尽量不用“嗯”或者“好”之类的单字去回复。
那年去过医院后的宁玺,疲惫地回到家。
宁玺走了一学期,宁玺妈妈很少给宁玺打电话,宁玺每周打过去也不接,偶尔接那么一两次,也是说“都好”“都好”,便挂断了电话。
宁玺十岁的样子,眉眼跟如今不太像,温软许多,但表情仍是冷冷的,靠在最边角的树旁,浓荫投下一层阴影,就在要按快门的时候,那会儿才七岁的行骋,扭过头去,看向了那棵树。
到了屋内,灯光亮堂些了,宁玺才看清楚,那黑玫瑰是行骋拿纸扎的,细看歪歪扭扭不成样子,花瓣下包了根金丝条,扎得乱七八糟一团糨糊。
行骋说:“曦雨,你先回去,明天我帮你约。”
“曦雨,我跟你说了,他喜欢传统的,淑女的,比他大的……”
宁玺侧过脸去看窗外的景,发觉他的小半辈子,就这么交代出去了。
宁玺上手掐他的脸颊:“不行。”
大年初三的晚上,宁玺被行骋看着早早就入睡,说是春节风俗,别瞪,得按着来。
独一无二的一,万里挑一的一。
这下倒是戳中了行骋的痛处,他板起一张脸,声色俱厉地道:“做题这种事看缘分,今天黄历说宜吃喝玩乐忌写试卷,那我跟它们就是有缘无分,等有缘了再写。”
行骋不依不饶地说:“你要是喝腻了怎么办?”
其实行骋都做了一大半了,二十张试卷,还剩几张政治的,可惜他实在没有那个觉悟,做这种题纯靠编,说些流氓话,净挨老师骂。
行骋一转身,球一甩,还不小心打到旁边的灯杆,他还跟着“嘶”了一声,低声说了句“好痛”。
行骋说完,伸臂去抓宁玺的手腕,直接把人拽到自己身边,一侧身挡住宁玺的半边脸:“你喜欢,你就去约他,你找我哥出来帮忙没用,应与臣只看我哥,不看你。”
“哎哟,宁玺来了啊,”大姨的金棕卷发久未打理,使她看起来憔悴不已,指尖还捏着颗剥好的提子,见着宁玺就要往他嘴里塞,“你先进来,你妈妈睡着了。”
行骋虽然高壮力气大,但宁玺好歹也蹿到一米八左右,没走几步行骋手就软了,开始出馊主意:“哥,我背你回去,你要是不好意思,就把我帽子掀起来遮脸。”
宁玺把花攥在手里,想塞回去又想自己收着,翻过来拿花杆往行骋头上一敲:“寒假作业做完了吗?”
宁玺沉着声说完,喉咙被堵得哽塞。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
——延年益寿谁不想,只是想和你一起长命百岁。
宁玺浑身发冷,想去摸兜里的烟,又想到这里是医院,便闷着头往前走,完全急于要逃离这个地方。
耳边的风太大,宁玺没听清这句话,只是捂着脸骂:“你人来疯!”
宁玺的脸闷在行骋校服领口边:“我也会。”
当初任眉天天上课揪着他,动不动就说要给宁玺打小报告,行骋像被戴了紧箍咒似的,立刻坐正,抄起笔记本就写黑板上的公式,当然,三天打鱼晒一百天的网,后面专心当护草使者去了,还真hetushu.com.com影响了他学习。
行骋伸手冰了一下宁玺的脸蛋,没多少温度,刚想说话,又看程曦雨这丫头还戳在这儿,看样子,她压根没有要走开的意思。
行骋憋着笑,悄悄对宁玺说:“以前,我打比赛,一累得不行,他们会喊你的名字。”
那里的人,那里的事,催促着成长的脚步,跑到了尽头,再消失不见。
行骋倒不以为意:“你要不要再试试看我下手狠不狠……”
两个人几乎是摸黑跑进楼道,灯都没给一嗓子吼亮,扒在门缝边,行骋手忙脚乱地从自己书包里掏钥匙,这钥匙是宁玺走之前留给他的,他一直带在身上,想起来了,偶尔进去坐坐。
行骋在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对宁玺,仍旧是那个上天入地的大男孩,急着把最好的都给他,再急着成长。
家里书架上还摆着合照,上面是小时候院里经常一起出来玩游戏的小孩们,年龄从三岁到十三岁的都有,身高落差大,行骋年纪小但蹿得高,直接抢了最中间的位置。
“得,我说不过,走为上策。”行骋被说得头疼,半个字也不敢堵回去,抓着试卷去开家门。
后来爸妈问行骋为什么往后看的,行骋只说是想看那棵树结果了没,叶子落了多少……
回来的第二天,宁玺一大早给妈妈打了个电话,那边接线的是大姨,说转院了,要去看的话,得坐公交车多少路,再换乘,下了站坐个小三轮,五块钱就到了。
行李就这么被他们暂时寄放学校门口的小卖部里,这冬夜里风大,回家的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路上偶尔遇到认识的同学,行骋只说有人发烧了。
行骋一听他哥讲这话逗自己,咬着牙说:“安,我今天就安!”
应与臣跟行骋都是混世小魔王,得亏有他在中间拦着,隔着,举一把秤,不然进校队第一天敢上房揭瓦,第二天敢开瓢打架,非得成一双天敌,比谁克死谁。
行骋把作业找出来压平,摁了两支笔出来,想了一会儿又塞了一只回笔筒里。
行骋爸爸开的悍马H2平缓地驶过往日他们最爱骑车过的滨江东路,行骋偏过头去看府南河,宁玺也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只看到河面波光粼粼,有几盏路灯不太亮。
后来,很多年匆匆而过,每逢除夕,成都不再下过雪,宁玺还记得他和行骋最开始的那两年,疯狂、迷惘,那会儿还是最年轻的他与他。
如今身边有重要的人,锦绣前程,未来可期,总有挑战的意义。
宁玺憋着笑想骂他。
她说完,宁玺把米汤接过来,笑着说:“行骋长大了也很优秀,招人羡慕。”
北京大部分高校的寒假放得比高三早了半个多月,再加上妈妈催着他,宁玺便买好高铁票,提前两小时就到了车站。
行骋在楼道里,把灯吼亮了,去捏他卫衣袖口下藏的指尖,说:“我爸妈让你上楼吃团圆饭。”
宁玺开始每天早上往妈妈那里跑,偶尔买些水果过去,大姨收了他私下给的一些钱,倒也更愿意帮忙照顾着。
行骋试探性地问道:“明天你要去医院陪阿姨吧?”
她也跟着乐,眼神转着弯在儿子身上打量,嘴上也不饶了他:“你这种小孩,招人嫌,宁玺那种,就招人疼。”
宁玺半睁开眼看他,低声说:“一起喝啊。”
宁玺往前挪了几步,把提子吐在纸巾上,叠起来扔进垃圾桶,“嘭”的一声。
他七点自然醒了一次,洗漱完又钻回去睡回笼觉,这下彻底醒了,但还是困倦,回来待这段时间,人都开始犯懒。
行骋插锁插得急,弄几次弄不进去,宁玺实在看不下去,一把夺过来开了门。
行骋这臭小子,之前还骗他说不冷,明明就是旱冬来了,盆地降不下雨,风往脖颈里狠命地刮,冷得干燥刺骨。
大姨像是在吃饭,那边市场吵闹得过分,拿着电话也恼,但还是免不了对外甥一顿叨叨:“地址我发你微信上!宁玺,你们家出了个北大的,不得了啊,你妈妈收那么多红包,都不晓得拿出来治病哦?说是只能活半年了,没得治,她男人嫌,说是她私生活不检点……”
喝腻了怎么办?喝腻味这事宁玺就没想过。
宁玺点点头,怕行骋想跟他一起去,迅速换鞋,被拖着就上了楼。
“别贫!”宁玺下巴一抬,指挥他,“试卷写不了,那你写作文。”
在外念书的人,总是思乡的。从前大概并不觉得家乡有多么好,可一旦离开了一段时间,便开始想念家门口转角卖的二两面条,初高中校门口一块钱一次的刮刮乐,或是一到夏秋之交,便急忙落了满地的树叶。
这种东西,对小孩的胃来说,或许确实不好,但宁玺就是忍不和*图*书住想多尝几口,这还是妈妈给他买的。
大姨估计是闷得久了,难得有个小辈来陪她坐着,找了梨来削,边弄边说话,把病历递给宁玺,他看得费劲,大姨又挨个跟他讲……
在这种充斥着希望与绝望的地方,在冬日的凛冽里,等了自己多久?
身边的亲戚他本来就接触得少,倒是考上好大学之后,莫名其妙多了几个来嘘寒问暖的,妈妈那边的亲戚更是不怎么熟,从小自己咬着牙撑大的,宁玺一面对长辈,难免局促,找了个板凳坐下来。
这么甜这么酸,咽下去一口气往头上冲,他舍不得这味。
行骋正纠结着,就看到妈妈站在房间门口,手里的罐里还拌着酱瓜:“儿子?你倒腾什么呢?”
“这口号喊了三年了,怎么就没腻。”
她连拿个苹果手都发抖,抬眼一看是行骋,眼里平静无波,只是淡淡地喊了一声:“行骋来了啊。”
就像宁玺长这么大所接触过的人,“对他好”与“不好”,他都明明白白,但只要一扯上亲情,这个界限便变得模糊不清。
那几个哥们一脸诧异,四周黑漆漆的,硬是没看出来背上的是宁玺,也没想到是谁,笑容暧昧,挎着书包吹上口哨在后面追着喊:“骋哥牛!”
宁玺毫不留情地呲他:“因为你傻。”
其实宁玺心里明镜似的,他是白天在医院照顾了妈妈一天,行骋担心他太累。
弟弟的硬茬子脑袋又剃了短寸,夏天晒黑的皮肤白回来些,校服拉链还是吊儿郎当地拉了一半,或许是因为训练辛苦而消瘦了,下颚线条有棱有角,锋利不少。
全程宁玺闭着眼没有睡着,心思全在手心上,在感受行骋比画了些什么莫名其妙的。
这书还是宁玺在北京没事每天趴书桌上抄的,全是他高三高考总结的一些重点,强调句用红笔勾画得鲜艳,封皮写了行骋的名字,力透纸背,那微微的凹陷总让宁玺忍不住,想用指尖触摸。
行骋是爱球如命的人,那雷霆的队标要是落了漆,不知道得郁闷成什么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边女孩大多泼辣敢做,听了这话差点儿跳起来,兴奋地去捏衣摆:“约约约!你跟他说!明天下午四点太古里百丽宫,我等他!”
试卷写着写着,就写到草稿本上去了,宁玺本来看行骋这漫不经心的态度,想发火,又觉得算了。
成都东站宁玺第一次来,大概因为返程巅峰,都九点钟了,地铁站人也非常多,他还好,个子算高,行李也少,才得以挤上去。
宁玺就这么趴在行骋背上,难得温顺而服帖,没有板起脸,没有冷着眼,只是用脸蹭他的校服,再评价一句:“行骋,你那只螃蟹呢?”
宁玺还记得,小时候,捧了碗水果刨冰站在家门前,行骋拎着小汽车模型飞奔过去,又慢慢倒退回来,一副小大人做派,正色道:“宁玺哥哥,我妈说这个凉胃,你别吃太多!”
回家后,行骋从衣柜里拎了件大衣出来给宁玺披上,两人出门去小区外面的连锁超市找地方充了水电费,再添了些生活用品,另外,依旧是带着那两罐汽水,又慢悠悠地晃回家里。
宁玺有点觉得电话里的大姨和坐这儿的不是一个人,他也不觉得自己多招人疼,被过分关心了反而别扭,他安安静静地不再讲话,手里捧个梨,等着他妈妈睡醒。
坐公交车慢慢回家的路上,他们找到最后一排的位子,行骋让宁玺靠窗坐,两个人的肩膀跟随着坎坷不平的公路,摇摇晃晃,起起伏伏,最后撞到一起。
宁玺乘着地铁才过了一个站,又觉得太慢了,提着箱子跑出地铁站,打了车就往小区的方向赶去。
“初中画校服后面的那只螃蟹,表示你横行霸道,现在不画了?”
医院门口的人流量特别大,他穿梭在人群中朝前跑了几步,站定,伸手去拍行骋的肩,待他转过身来,再紧紧抱住。
行骋倒像真在思考,摸摸下巴道:“也不是不行……”
行骋跟着挤进来脱鞋。
宁玺二十一年来对“母爱”的理解太过复杂。
“行了!”宁玺推了行骋一把。
“红石榴味的。”宁玺懒懒地答。
好一会儿行骋才想起来自己是带他去吃饭的,把手里两瓶饮料举起来:“哥,这牌子出了新的口味,青柠的,我一个买了一瓶,你要哪个?”
行骋看着他哥闷着脸站在门口,伸手去关门了,又扒着门边哄他:“哥,我写个游记吧?玩也玩了,作业也写了。”
他们班主任还教育过:“你们高中,要不然好好谈个恋爱,要不然好好考个大学,不学无术吊儿郎当,没个正经样子,白白浪费三年做什么?”
行骋飞奔下楼,一头扎进房间里翻寒假作业。